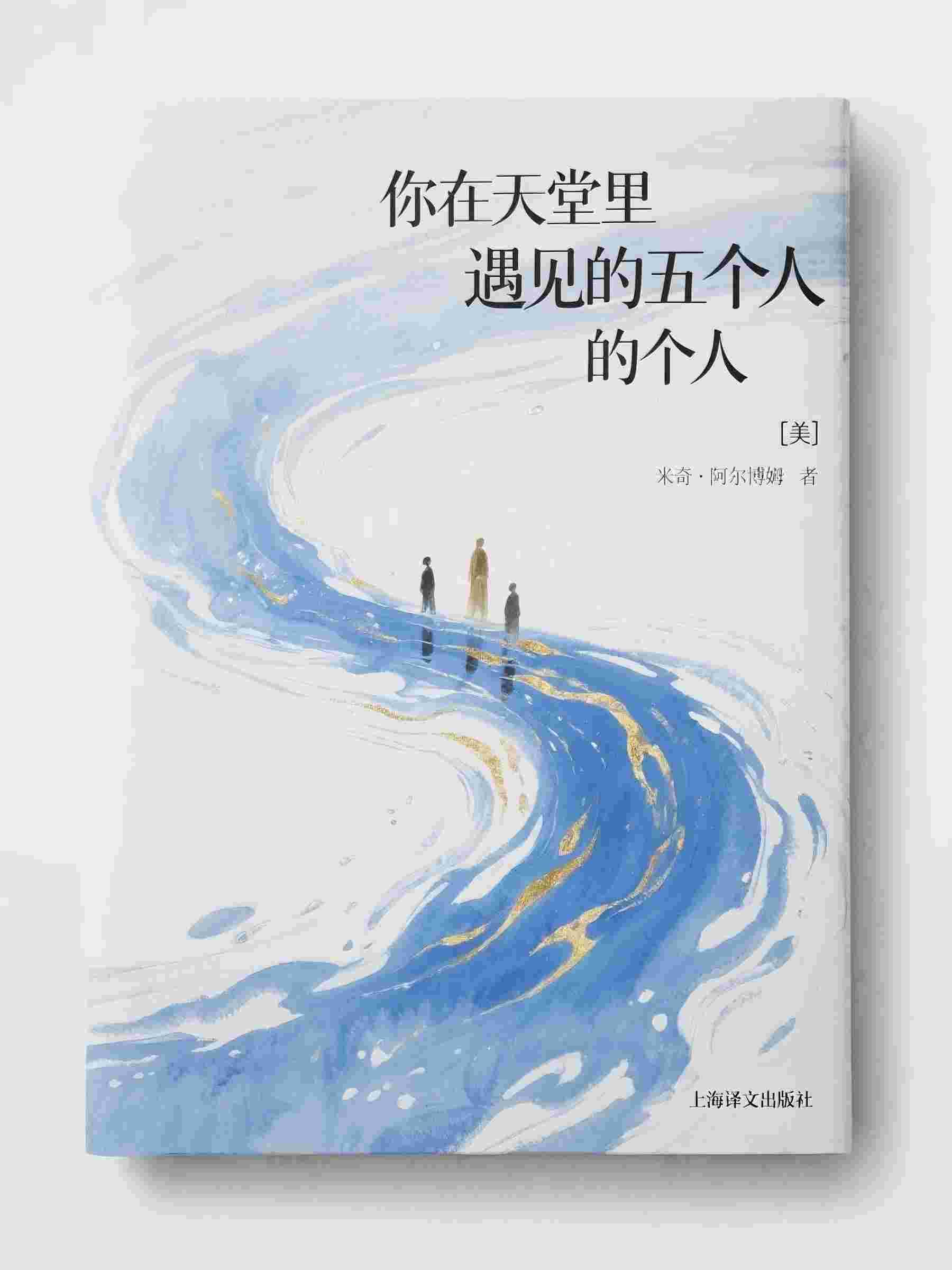我视线顺着他腹部的手看下去,看着他敞着大衣毛衣之下被休闲裤包裹着的某个地方。
“你要是敢动那套房子,老娘让你断子绝孙!”
机场里的陌生人已经围了过来,拿出手机“咔嚓咔嚓”拍着照片。
我来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相信不久之后这事就该上新闻了。
趁着还没有记者过来,我小跑着离开了机场,一个人开车到了机场旁边一个毫无人烟的地方放声大哭。
有的人说雨夜里哭泣的人是最可怜的,可我觉得,在熠熠星光和朗朗月色下哭泣的人才最可怜,因为连老天爷也不肯给一场应景的雨。
罗立找过来的时候,我正在打着嗝,眼睛肿成了一条缝。
他蹲在我面前,没有因为我的难过选择感同身受地安慰,眼睛弯成了月牙儿,亮着他的手机,上边儿是我在机场打许庭安的照片。
“冉冉姐为什么要打人啊?”
他柔声问我,像个明事理的家长在面对无理取闹的孩童。
“他、他要拿走、我、我给你娶、娶媳妇儿的、房、房子。”
我抽抽噎噎回道。
他把手机装回了口袋:“那是该打,怎么能动我和冉冉姐的东西呢。”
我和冉冉姐的东西。
这句话真的是莫名的戳人。
继续阅读请关注公众号《森树轻阅》回复书号【9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