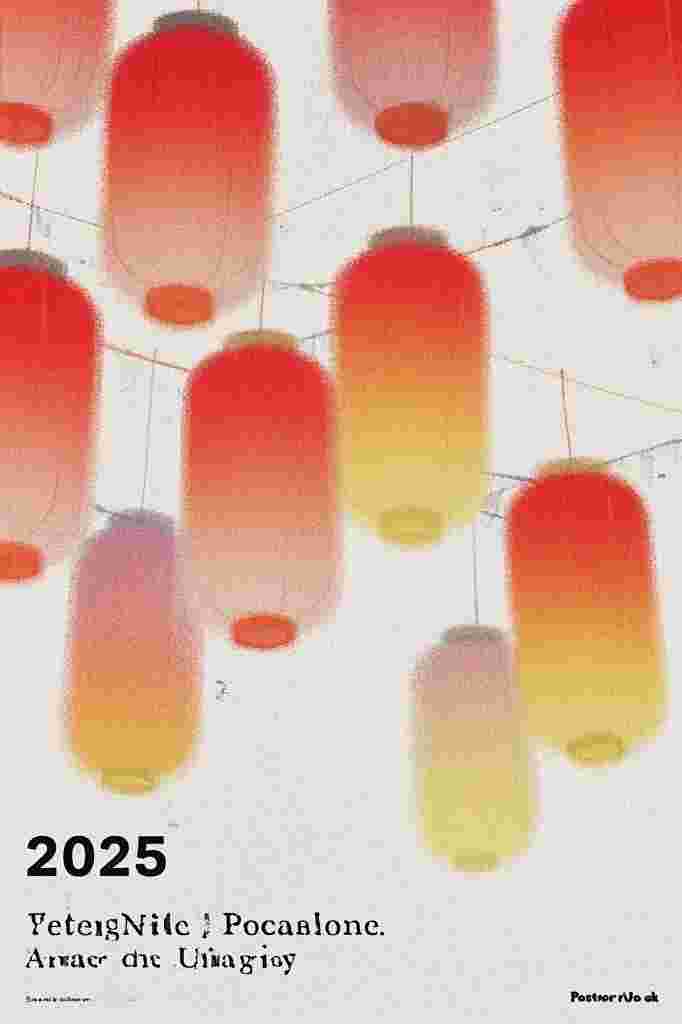,而我的态度也渐渐冰释,偶尔是说笑,偶尔是帮忙做下家务,还给继父的单位送过员工餐,一切都显得很好,当然,如果没有那每天夜里的窥探和监视,我没准还真以为她对我还有爱。
他们通常会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商量计划,继父最近频繁地收到一些来历不明的礼物,而且还经常在接到神秘的电话,而这一切在我晚上收摊回家后都会统统消失。
当然,针孔摄像机不会放过这些画面。
我的摆摊事业如火如荼,时间也快来到今年的高考季。
今天母亲端来红枣银耳羹时,窗外的路灯正巧坏了,她手腕上的银镯子磕在瓷碗沿,发出类似镣铐的脆响。
我数着老式挂钟的滴答声,看她在昏暗中搅动汤匙,糖水表面浮着的枸杞像凝固的血珠。
我看了眼她,没做迟疑,一碗糖水顺喉而下。
下肢麻木感从脚踝攀上膝盖,

重生后,全网求我别摆摊全章+后续
推荐指数:10分
周文热门是现代言情《重生后,全网求我别摆摊全章+后续》中涉及到的灵魂人物,二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看点十足,作者“ok虎娘娘”正在潜心更新后续情节中,梗概:我死在高考出分夜,凶手是把哮喘药换成面粉的亲妈。重生回高一誓师大会,我当众撕碎市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走向校门口煎饼摊。“我这是……重生了?还回到了高一誓师大会这天!”我掐了掐自己的胳膊,钻心的疼让我确定这不是梦。刺眼的阳光穿过教室的窗户,直直地打在我脸上,照得我眼皮生疼。我悠悠转醒,映入眼帘的是满墙......
第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