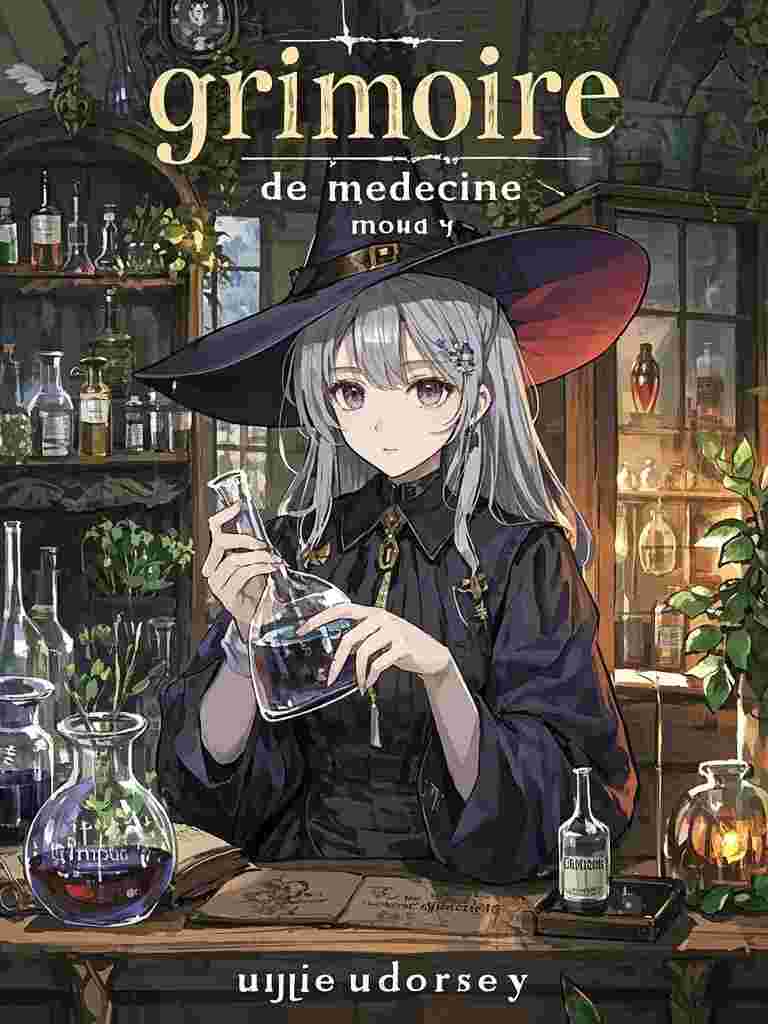闻蝉轻轻点头,终于放下一笔心事。
檀颂却还觉得愧疚,主动道:“那程家的事可了了?夫人既说她们不追究,那不妨我今日便登一趟门,说几句场面话,将此事了结作罢。”
“不可,”闻蝉却说,“她们指望我游说谢御史,可当日登门,我却受了冷待,你此番去不好交代。”
“那要怎么办?”
闻蝉道:“自是等着她们程家,主动登门。”
如今这关头,该是冷一冷程家,叫她们顾自担惊受怕一阵,届时再软语讲和,两家才好不伤情分。
第二日,程家便来人了。
不过不是谁登门,而是递了请柬,请她们夫妻二人至程家的庄子里,一同迎冬炙羊肉。
闻蝉看出了些不寻常,想到,谢云章兴许也会去。
果然,当日的庄子里,程知府与谢云章把酒言欢,已然是冰释前嫌的模样。
而程湄也露面了,手臂应当还没好全,但从外表看,已然看不出什么。
程夫人一扫阴霾,对着闻蝉道:“得亏你替我奔走,不然今日保不准,这谢御史还不肯卖这面子呢!”
话虽这样说,可她语调并不真心,可知是程家自己想了法子。
或是说,当日惹恼了谢云章,这程家的人情,谢云章故意不给她。
“檀夫人来,咱们去给谢御史敬杯酒,算是冰释前嫌了!”
程夫人一出声,闻蝉依言转头,恰好对上谢云章侧目望来。
他金冠束发,织金云纹的锦袍外头,还裹着白裘,好不富贵旖旎的从容模样。
见了她也只道:“不是说了,别请她来,程夫人这是不卖我面子?”
谢云章可没说这话。
彼时程夫人试探,说不如将檀家夫人也请来,谢云章怪声斥了句“请她作甚”,可不就是想她来的意思。
程夫人不傻,经了这许多事,就算说不准她二人私情,也看出谢云章对人另眼相待。
她纵女犯下错事,正愁无处赔罪,若能借花献佛,叫谢云章遂了心愿,得了闻蝉,前事自不必再提,保不准,还能得人一番答谢。
不过这些都是她暗自揣测的,事态究竟如何,还得走一步看一步。
“谢御史何等肚里撑船的人物,竟和一个深闺妇人计较起来?”
程夫人回身来携闻蝉的手,“通判夫人来,咱们一道敬酒,把话说开了便是。”
上回闹了个不欢而散,叫谢云章半途扔她下车,闻蝉此刻也有些吃不准,他究竟是个什么心思。
正要去接酒盏,却被身侧人一把夺过。
“夫人近来身子不适,还请御史大人宽宏,叫我替夫人饮了。”
说罢,仰头饮下盏中酒。"

成婚三年,世子掐腰哄我改嫁免费看
推荐指数:10分
《成婚三年,世子掐腰哄我改嫁》是难得一见的高质量好文,闻蝉谢云章是作者“明珠不语”笔下的关键人物,精彩桥段值得一看:“养你七年,是为你在旁人榻上承欢?”闻蝉是三公子养在掌心的娇花,自幼苦学琴棋书画,只为换得男人唇畔一抹赞许。可三公子生在云端,既要侯府贵女做正妻,又要她伏低做小为妾。逃婚夜,她烧了为他绣的嫁衣。重逢时,她披着他人妻的霞帔。五年光阴,将昔日温雅矜贵的少年郎,淬成了阴鸷强势的权臣。在她与夫君的婚房中,男人指尖冰凉,薄唇热烫,辗转吻过她颈间红痕:“不想做寡妇,我教你写和离书……”那夜女子雪白的脊背上,朱砂印泥混着汗水淌入脊骨。触目惊心,是五年前她不告而别,留给他的诀别书。...
第7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