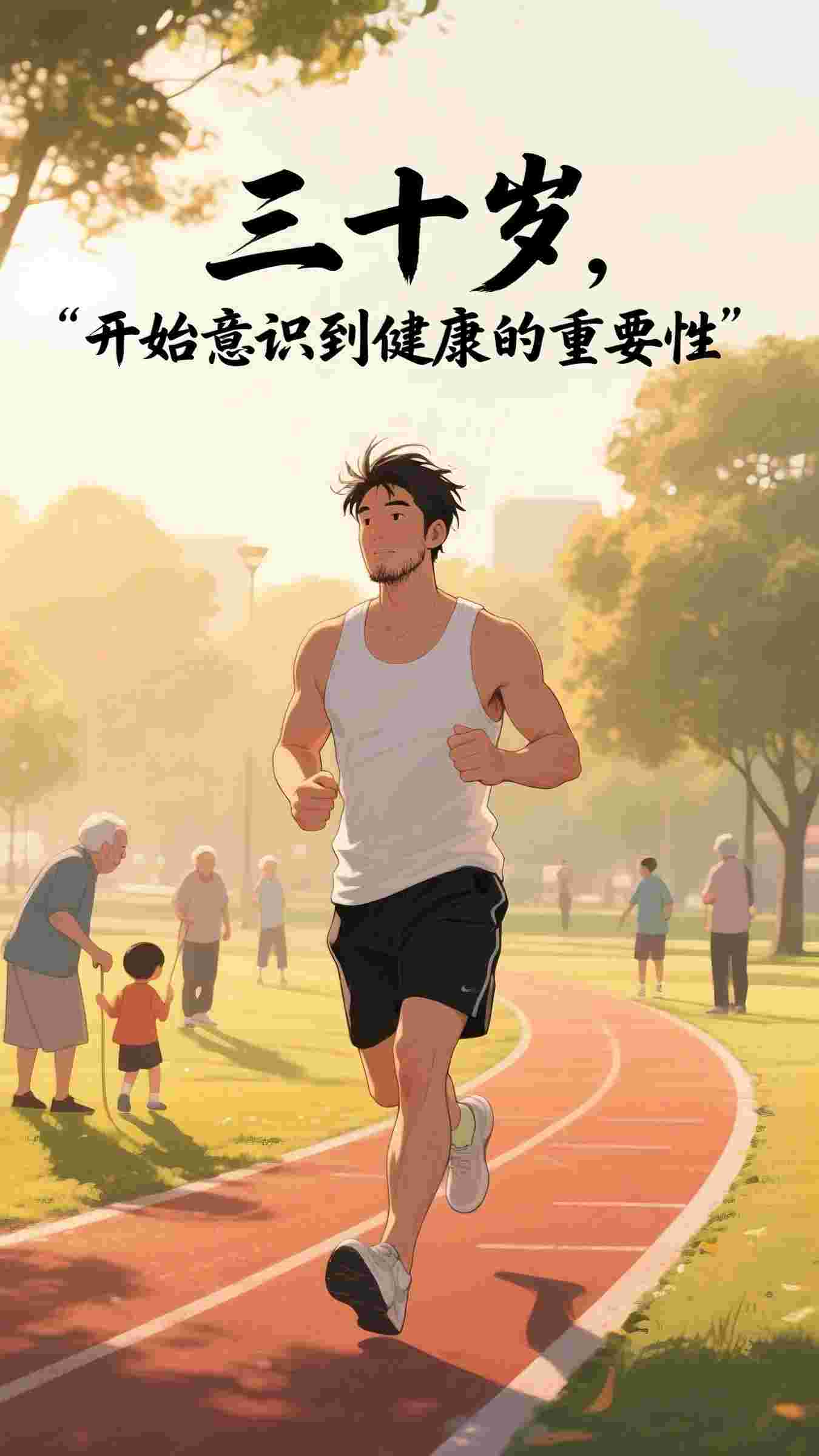藏着很多很多,我看不懂的情绪。
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不是关于病情,不是关于费用,而是关于……我们。
他似乎有些紧张,飞快地低下头,抱起馒头,几乎是落荒而逃。
我捏着那本病历,看着背面的画,久久没有动。
松节油,烟草,漫画家,沉默,伤疤,还有这颤抖却精准的线条……林深。
我在心里默念着从芯片信息里看到的名字。
从那天起,林深每次来复诊,我们都会在病历本背面“画画”。
有时是他先画,有时是我先画。
他会画馒头在家里调皮的样子,或者窗外的风景。
我则会画些诊所里的趣事,或者天气。
我们从不交谈画的内容,但彼此都心照不宣。
这成了我们之间一种奇怪的默契。
他的画依旧线条颤抖,但越来越放松,内容也越来越生动。
通过这些画,我零碎地拼凑出他的生活:他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与画笔和颜料为伴。
馒头是他唯一的“室友”。
但我更好奇的是,他为什么沉默?
那些伤疤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反复遗弃馒头?
这些问题盘旋在我心头,但我没有问。
我知道,时机未到。
馒头的伤彻底好了,不需要再来复诊。
最后一次检查结束,林深在病历本上画了一个小小的蛋糕,旁边写着谢谢叶医生。
我看着那行字,心里有些失落。
这意味着,我们这种奇怪的“便利贴日记”也要结束了。
“以后……”我顿了顿,“如果馒头有什么不舒服,或者你想找人聊聊,随时可以来。”
他抬起头,看着我,有些惊讶。
然后点了点头,然后,用备忘录打了一行字:你也一样。
他走了。
诊所又恢复了往常的忙碌,但似乎少了点什么。
我开始控制不住地想起林深。
想起他沉默的样子,他手腕的疤,他颤抖的画笔,还有他看我时,那双深潭般的眼睛。
我决定做一件可能有点出格的事。
连续两周,我会在下班后,开车到他公寓楼下。
不做什么,只是在车里待一会儿,看看他家那扇亮着灯的窗户。
我知道这很像个变态,但我只是……放心不下。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每晚十一点左右,他都会走到阳台上。
他家的阳台是全景玻璃,从我这个角度,能隐约看到

诊疗室里的沉默法则全文无删减
推荐指数:10分
主角叶哥小李出自现代言情《诊疗室里的沉默法则全文无删减》,作者“北海渔民”大大的一部完结作品,纯净无弹窗版本非常适合追更,主要讲述的是:【双男主】一:第七次遗弃事件凌晨三点,手机尖锐地划破寂静。窗外是瓢泼的暴雨,雨点砸在玻璃上,噼啪作响。我揉着眼睛接起电话,是动物保护站的小李。“叶哥,又是‘馒头’。”小李的声音带着疲惫,“第七次了,在上次那个公园门口的垃圾桶旁边找到的。”我叹了口气,披上外套:“知道了,送过来吧。”挂了电话,诊所的灯......
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