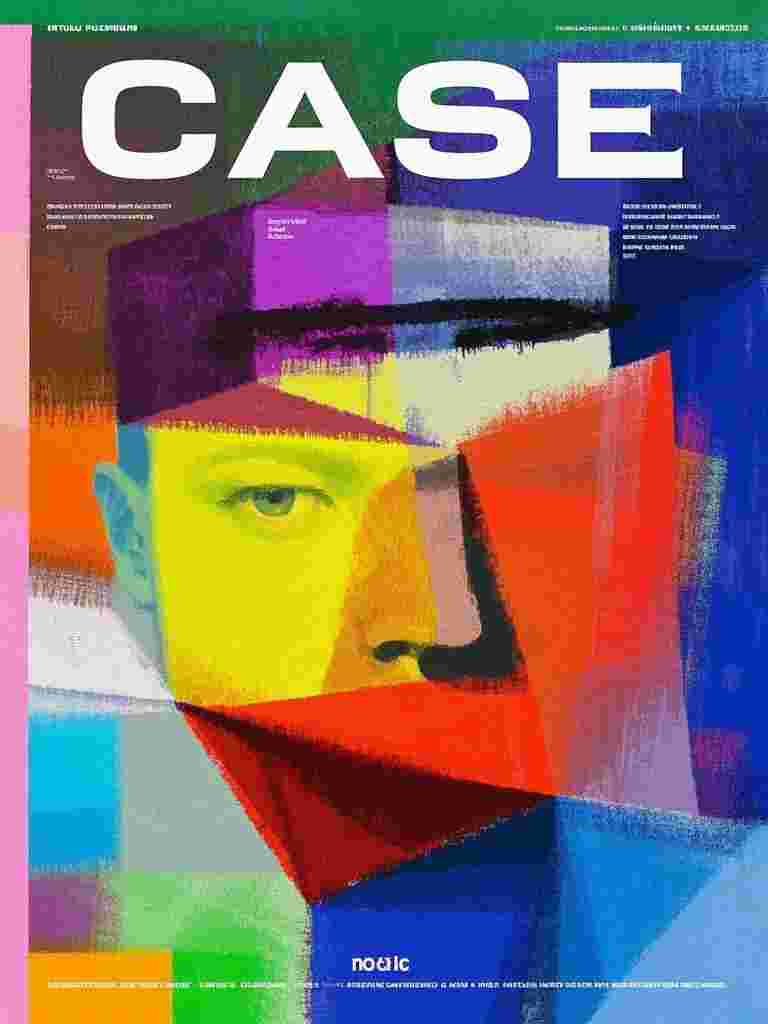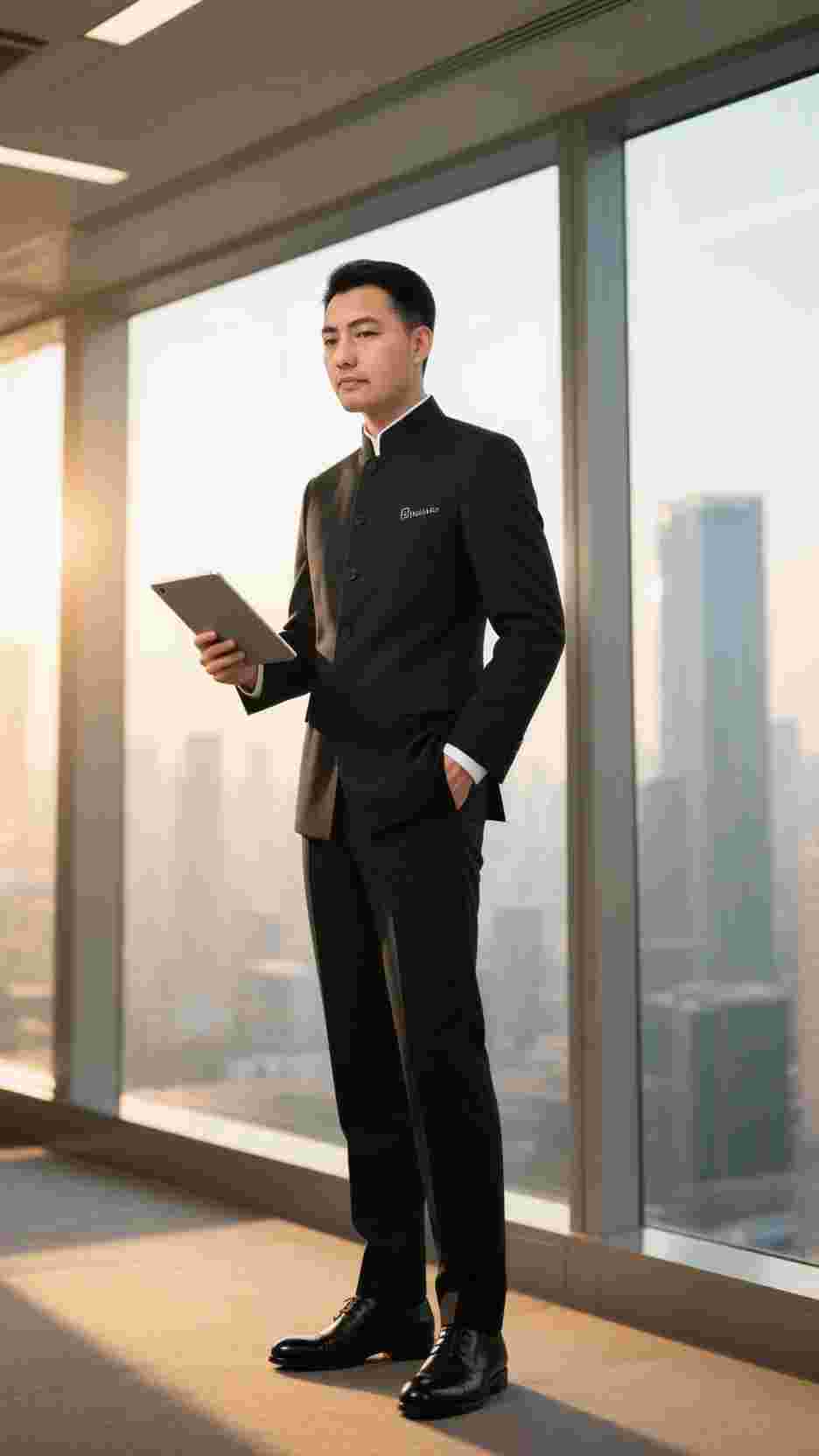时候可不自在喔。”
“云南美景那么多,犯愁的时候可以随时出去透透气,多好!”
“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旅行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跑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在这里待久了,的确会腻的。
束河虽然比大研安静许多,做生意竞争没那么激烈,但相应地,客流也没那么多。”
“想要两全其美,确实是难事。
我明白要对一个地方保持恒久的激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毕竟有旅行这种方式,偶尔出去走走,换一种心情,恢复动力后再回到原地继续生活下去。
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我的激情是通过在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之间替换而获取的,或许是我过于重视新鲜感这种东西,然而我又很清楚新鲜感和激情一样是会消退的,于是常常容易陷入一种矛盾心理,似乎我追求的东西永远不确定,永远在别处。”
“可是人生的精彩不正是在变动之中产生的吗?
当稳定成为常态,那不就是死水吗?
我热爱旅行,其实就是一种调剂,尽管我知道远方不一定就比此处美好,却仍然一再选择上路去一探究竟。”
“那看来还是你比我通透。
我觉得自己是迷茫了。
可能是因为年纪的关系,都说三十而立,我却还是漂泊四方。”
“我其实相当反感按照某种约定俗成的惯例或习俗,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好像人生就只能循规蹈矩按照指令完成一项又一项被布置好的任务。
人生不应该存在所谓的时间表,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要走同一条路的呀,为什么不允许例外呢?”
我虽未言明,但这无疑是为自己信奉的独身主义辩护,然而我看见敖绍城的眼里闪过了一丝疑虑。
“从出生走向死亡,我们不是都在走同一条路吗?”
他陡然将话题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层次,我惊诧不止,一时不知作何回复。
我并不是顾忌谈论“死亡”,而是他那话头里蕴藏的现实意味让我愕然。
彼此沉默了两三分钟,然后我转换了话题,聊起了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情。
我们谈到仍旧保留母系社会制度的泸沽湖,对摩梭族走婚这一习俗饶有兴趣。
“我感觉这种母系社会的传统婚姻习俗倒似乎比当代人更开明呢,没有一夫一妻制,也无需从一而终,若有

我曾以为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结局+番外+完结
推荐指数:10分
很多朋友很喜欢《我曾以为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结局+番外+完结》这部现代言情风格作品,它其实是“悬溯”所创作的,内容真实不注水,情感真挚不虚伪,增加了很多精彩的成分,《我曾以为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结局+番外+完结》内容概括:今年国庆假期,我打算独自前往大西北旅行,计划去甘肃和青海两个省份。我是个极爱抠字眼的人,对于每次的个人自由行,总要称为“旅行”而非“旅游”。在我看来,前者意指追寻心灵和精神层面上的格调趣致,后者却大多让人径直联想到公司旅游抑或市面上各色杂沓的跟团游之类,因而我本能性地排斥“旅游”这个词。部门已婚中年......
第2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