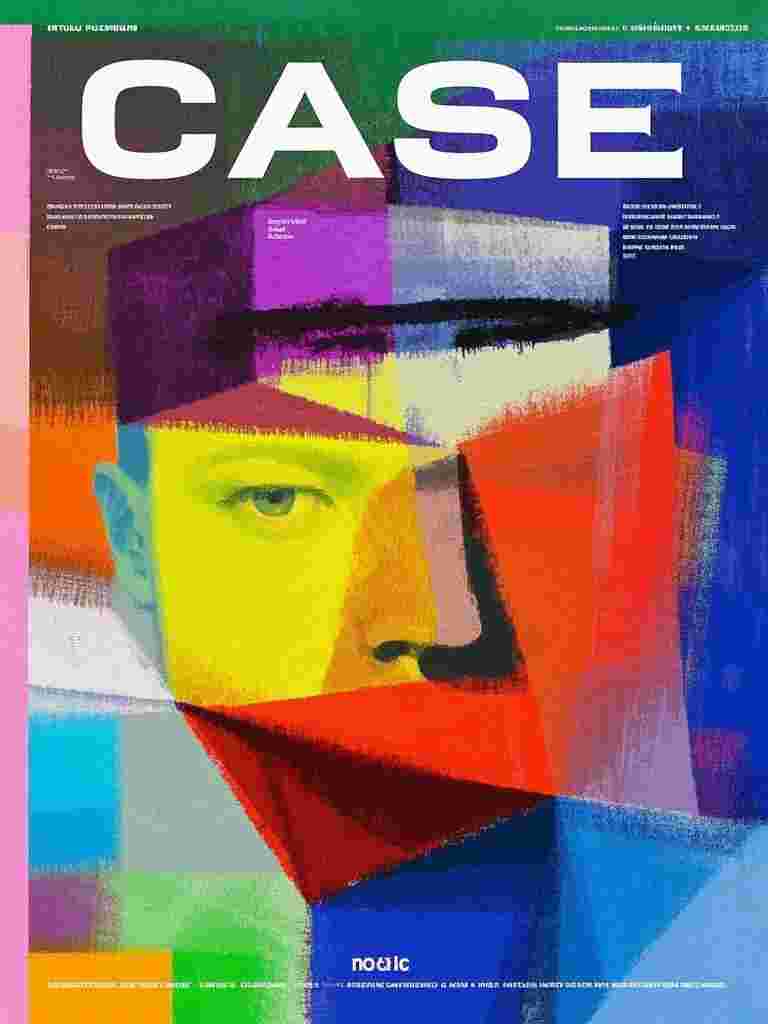这种欺负女人的畜生。
“我给孩子们报了舞蹈班,此时恰巧老师推门进来:“孩子们,去上课啦!
“双胞胎蹦跳着跟老师走了。
我站在窗前,看见警车里的霍凛正扒着窗户往舞蹈教室方向看。
儿子咯咯笑着转圈,后颈发际线处有个小小的旋。
霍凛被警察带走时,湿透的衬衫后领也露出同样的发旋,在阳光下泛着棕色的光。
雨突然下了起来,冲刷着玻璃上他模糊的影子。
警车拐过街角的瞬间,我下意识摸了摸锁骨上方。
那里曾有一道雪茄烫出的伤痕,如今早已淡得看不见。
就像那些年抽血留下的针眼,被时间抚平成细小的白点。
舞蹈教室的玻璃映出我的倒影,恍惚间又看见二十岁那年的自己。
第一次被带进霍家别墅时,他站在落地窗前擦手,血珠顺着指尖滴在地毯上。
“别怕,“他头也不回地说,“是鹿血。
“那时我竟愚蠢地觉得,会为猎物道歉的猎人也算有温度。
继续阅读请关注公众号《糖果读物》回复书号【23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