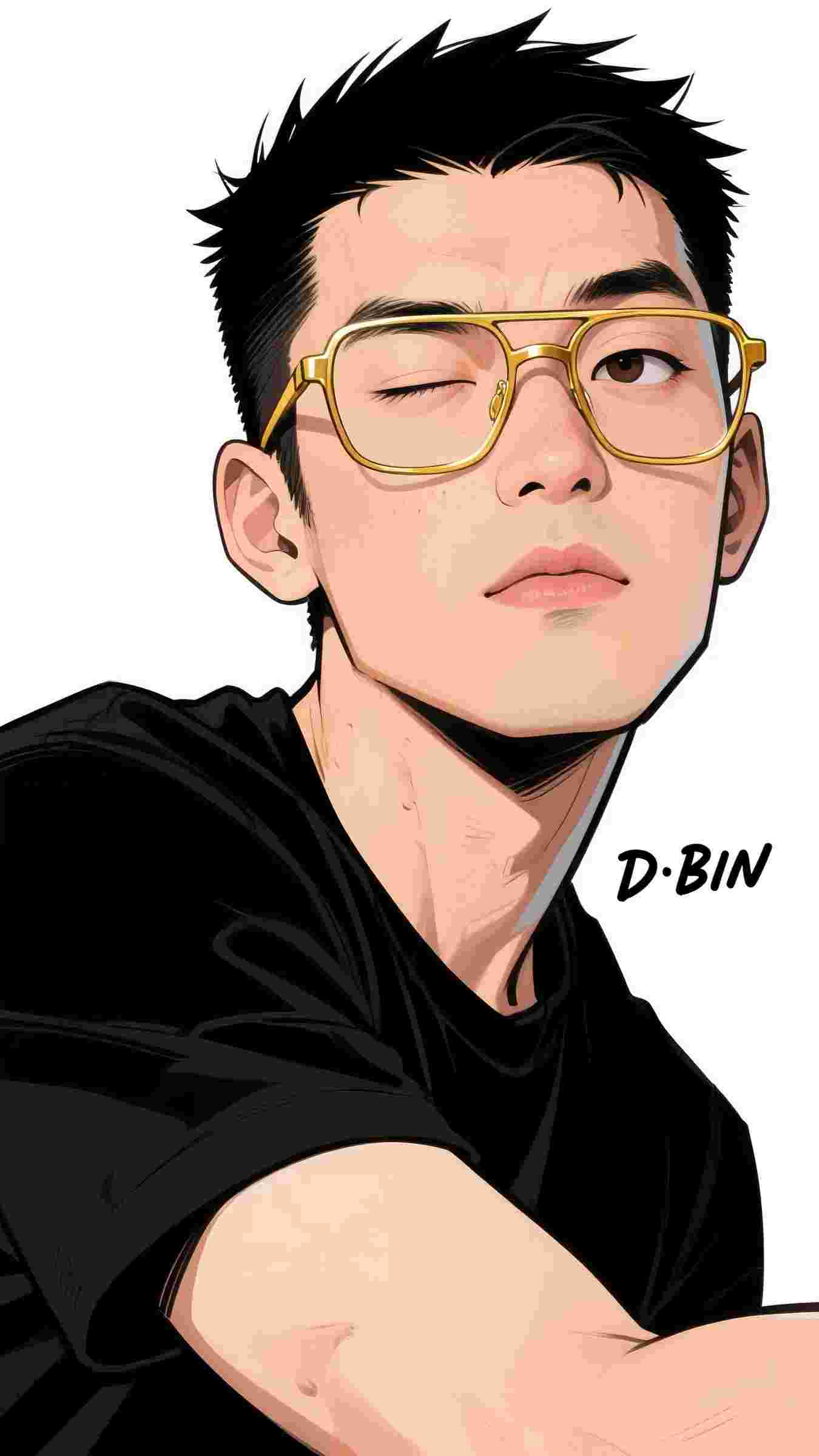他的手腕,掌心温度透过皮肤传来,带着经年习武的粗糙感。
“所以我要你随我去漠北,亲眼看着凌族子民安居乐业。”
他的拇指摩挲着苏砚修腕骨的旧疤,“砚修,别再做棋子了,做我的...谋士也好,知己也罢。”
苏砚修挑眉,却在看见对方眼底的认真时,忽然想起藏书阁初遇的那个春日。
那时这人斜倚在竹椅上,阳光穿过花窗落在他发间,像撒了把碎金。
他轻轻叹气,从怀中取出《止戈书》,纸页间夹着片干枯的海棠花瓣——那是去年春天,这人替他捡的落花。
“好,但凌族需退出长城以北,永不南侵。”
秋别长安的暮秋,凉意如针,丝丝缕缕地往骨髓里钻。
朱雀街上,送行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动,喧闹声此起彼伏,可这一切,似乎都被隔绝在萧承煦乘坐的马车之外。
他坐在车内,视线牢牢地锁在车帘缝隙外那个骑着黑马的身影上,思绪如乱麻般纠缠。
萧承煦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苏砚修送给他的玉佩,那温润的触感,仿佛带着对方的温度。
这块玉佩,本是前朝遗物,被苏砚修视作珍宝,如今却到了他的手中,这其中的情义,不言而喻。
他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苏砚修在藏书阁里为他讲解《左传》时的专注神情,在金銮殿上与他并肩应对朝堂纷争时的沉稳冷静,还有在那些漫长黑夜里,两人秉烛夜谈,探讨《管子》轻重之术时的惺惺相惜…… 桩桩件件,如同昨日之事,在他心头一一浮现。
“砚修,”萧承煦低声呢喃,声音轻得如同风中的叹息,“若能与你相伴余生,哪怕放弃这江山,又有何妨?”
然而,他心里清楚,身为帝王,肩负着江山社稷、万千子民的重任,许多时候,身不由己。
车窗外,苏砚修骑着黑马,身姿挺拔,却难掩落寞之色。
他身上的凌族兽纹披风,在秋风中猎猎作响,像是在诉说着他内心的波澜。
他望着前方蜿蜒而去的道路,心中五味杂陈。
此去漠北,萧承煦前路未卜,而他自己,也将面临更为复杂艰难的局面—— 岭南宗王余部蠢蠢欲动,朝中守旧贵族虎视眈眈,新帝虽年幼却心怀大志,这偌大的长安,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先生,”付恒将军不知何时骑

双雄错爱:江山与君皆难负:结局+番外
推荐指数:10分
《双雄错爱:江山与君皆难负:结局+番外》是难得一见的高质量好文,萧承煦苏砚修是作者“牛肉包没有牛”笔下的关键人物,精彩桥段值得一看:春劫大梁都城长安的暮春,连风里都飘着柳絮的黏腻。祁连王府的藏书阁檐角下,萧承煦正用镇纸敲着《左传》卷角,目光却透过镂空花窗,落在廊下那个青衫身影上。苏砚修正垂眸临帖,狼毫在澄心堂纸上游走,袖口挽起三寸,露出腕骨处一道淡青色旧疤——那是三年前替萧承煦挡刺客时留下的。“砚修,”萧承煦故意将书卷摔在石桌上......
第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