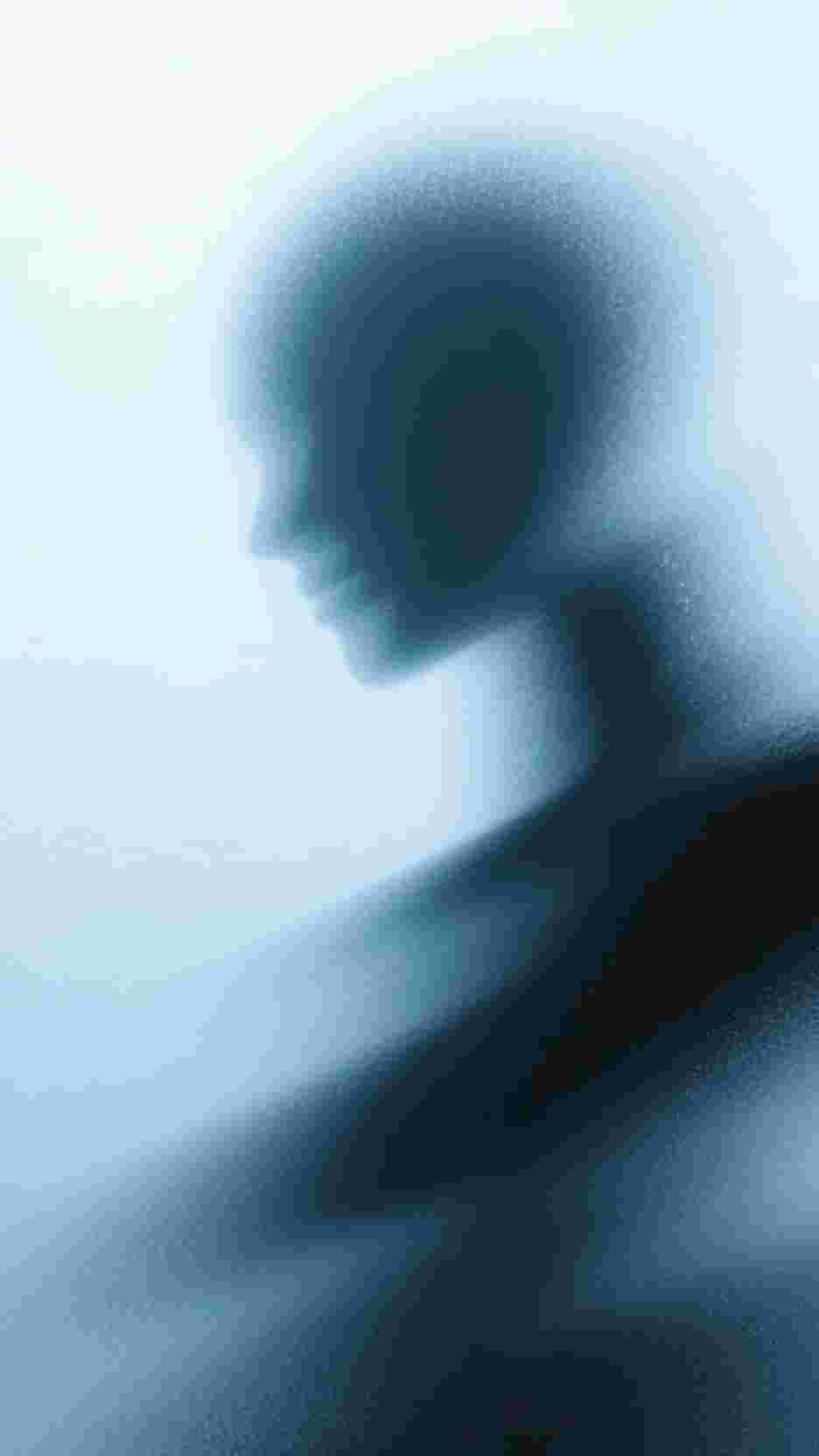自己厚着脸皮去太医院寻药,那些太医看到自己,就像是看到了索命的恶鬼一般。
奈何,都被她霍霍了。
“你……你是说,那些蠕动的活物都是药引子?”
她知道,想要缓解自己的病情,只靠草本药物是无法办到的,所以才松了口用别的辅助。
可是,也没有想到那东西那么奇形怪状。
胥月薄唇紧抿。
她本来不想让自家娘娘看到那些东西,届时熬出来之后她知道什么?
可惜,当时需要逼供的东西。
瞧着胥月杵在那里不说话,原本爬起来的姜姀,像是被人敲了骨头似的,又重新瘫了回去。
她望着帐顶沉思了许久,才不确定地询问。
“你说,会不会是你学艺不精,才需要那些东西当药引子?”
“或许,我的病情压根不需要那些东西?”
“……娘娘,您是不是忘了奴婢师承何人了?”
听着她质疑自己的医术,胥月的脸色瞬间便黑了,这绝对是主仆情最寡淡的一天。
姜姀双手捂着自己的耳朵,一副不愿意倾听的模样。
她自然知道胥月的师傅葛神医,当初祖父担心自己入宫后应付不来,专门让胥月学得医术。
那位葛神医的医术,确实可以活死人肉白骨。
若不是祖父与他们这一脉有些交情,胥月又颇有几分天赋,他怕是也不会收她这个徒弟。
“娘娘,良药苦口利于病。”
姜姀知她苦口婆心,可还是做着最后的挣扎。
“那已经不是苦的问题了。”
胥月被噎了一下,那可都是上等的药引子,旁人求都求不来的东西,她倒是嫌弃上了。
“您若是不愿意喝,奴婢也不强迫,可您的身体未必能撑得住。”
“届时,皇长孙若是还活着呢?”
徐晃的纸条她也知道,皇长孙若是还活着,到时候看到她这副模样该有多痛心疾首?
姜姀捂着耳朵的手慢慢松开。
她知道自己没有了矫情的资格,只是一时间拐不过弯来,毕竟比这更地狱的事情她又不是没有经历过?
乾元观的七年,可并未风平浪静。
桑婕妤的生辰刚过,太后的寿宴便摆上了日程,景淮则将这劳心费力的营生直接交给了姜姀。
并且给她透露——年贵妃和宋贤妃,寿宴上得现身。
瞥到他神色阴郁的模样。
姜姀明白,七年的时间世族又卷土重来,而帝王容不得没有界限的臣子。
这是后宫擂台,更是朝堂的博弈。
“你自幼便对后宫斗法了然于胸,朕相信你能做得很好,不辜负朕的期望。”
“听说,您最近盛宠焦御女?”
“年家送进宫的女人,朕可不得好好宠着?”
焦御女明面上是良家子,可派人细细去查却也能寻到蛛丝马迹,是年家的外室女。
只是那外室后来嫁给焦姓男子,这女子便随了焦姓。
“看来,年家被您养肥了,确实到了屠宰的时候。”
没了姜家挡路,这位上数三代还是寒门的年家,便成了真正的权贵人家。
人有了银子会眼高于顶,人有了权势会横行无忌。
现如今这位年家掌权人是年贵妃的父亲,虽然没有自己祖父那般履历,可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的。
人在往上攀爬的时候,最容易结党营私。
他现如今官至首辅却不懂得急流勇退,而是紧巴巴地拽着手中的权柄。
——帝王,又如何能容得下他?
景淮大咧咧地躺在软榻上,一身绯红色的常服将人衬托的略显妖异,就连笑容似乎都充满了不怀好意。

七年囚凤:皇后归来弑君嘉佑姜姀:全文+后续+结局
推荐指数:10分
很多网友对小说《七年囚凤:皇后归来弑君嘉佑姜姀:全文+后续+结局》非常感兴趣,作者“翊君”侧重讲述了主人公嘉佑姜姀身边发生的故事,概述为:她缓步踏入凤栖宫,指尖抚过熟悉的宫墙。七年前那场大雪夜历历在目——祖父饮鸩,父兄残废,家族百年荣光毁于一旦。宫娥们窃窃私语,她恍若未闻。当指尖触到凤椅雕纹时,往事翻涌。那个曾被她下毒未遂的帝王,如今将她召回宫中。她端坐凤椅,眸色沉静。既然太后和皇帝敢让她回来,就该知道,禁足七年磨掉的只是她的冲动,而非仇恨........
第2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