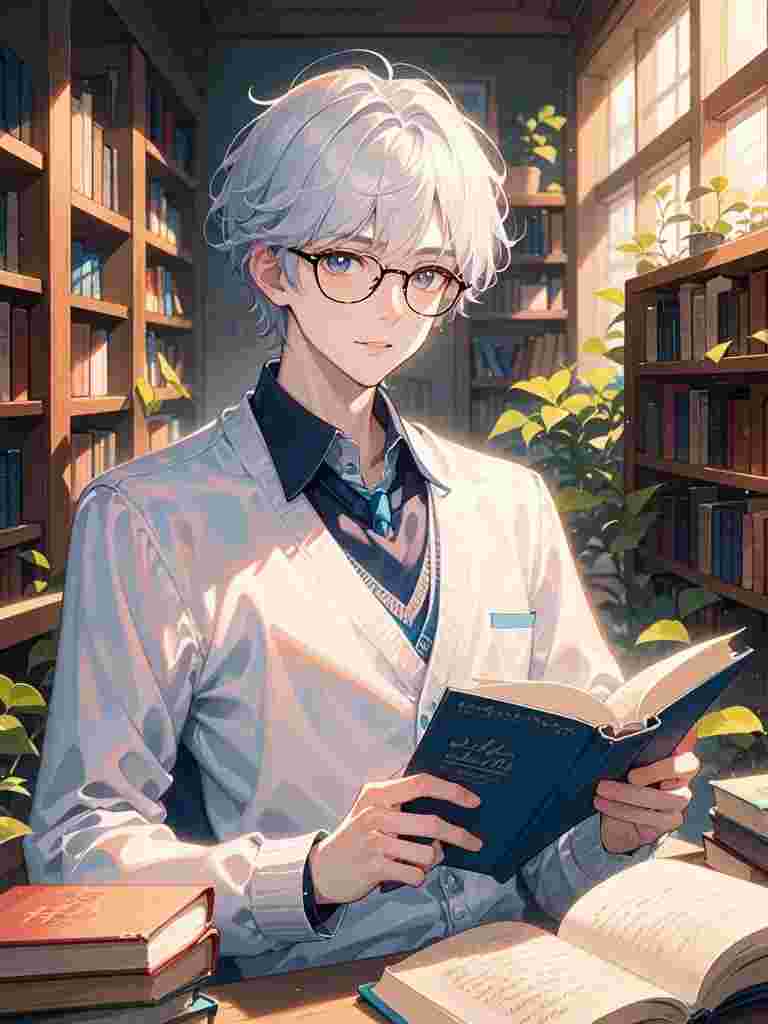据。
我微微侧过头,目光平静无波,如同看着一个全然陌生的人,落在那张因极度震惊和某种难以言喻的恐慌而彻底扭曲的、英俊的脸上。
嘴唇轻启,声音不高,却像淬了冰的细针,清晰无比地穿透了这凝固的、令人窒息的死寂,钉入每一个人的耳膜:“萧烬,”我看着他,嘴角甚至弯起一个极其细微、却冷到极致的弧度,清晰地叫出了那个我以为早已尘封在屈辱里的名字。
“原来你也知道,这是刀痕啊。”
--------8 悔恨深渊死寂。
时间仿佛被那狰狞的伤疤冻结了。
空气粘稠得令人窒息,连烛火爆开的轻微噼啪声都清晰可闻。
无数道目光,如同实质的针,密密麻麻地刺在我暴露的下半张脸上,又猛地转向萧烬。
那目光里有惊骇欲绝,有难以置信的厌恶,有对暴行的本能愤怒,更有一种看疯子的怜悯——对萧烬的怜悯。
南梁使团副使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哆嗦着,几乎要晕厥过去。
北燕的老臣们,则纷纷挺直了脊背,眼中射出冰冷、带着国仇家恨的怒火。
毁妻容,还是用如此残忍的刻字方式,在任何国度都是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已不仅仅是私德败坏,更将南梁使团、甚至南梁国格,钉在了耻辱柱上。
萧烬僵在原地。
他手中的剑还直直地指着我颈侧的方向,但剑尖却在剧烈地颤抖,带动着整条手臂都在痉挛。
他脸上的狂怒和疯狂如同被泼了一盆冰水,瞬间凝固、碎裂。
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此刻空洞得吓人,所有的情绪——震惊、不信、狂怒、绝望——都被眼前这活生生的、由他自己亲手制造的“证据”碾得粉碎。
他像是第一次真正看清我脸上的伤疤。
那扭曲的、粉白与暗红交织的皮肉,像一条丑陋的毒蛇,死死缠绕着他过去的记忆。
他仿佛又闻到了那个“洞房花烛夜”弥漫的血腥气,听到了刀锋割开皮肉的声音,看到了沈清秋——那个他从未正眼看过、只当作耻辱枷锁的女人——眼中最后一丝光亮熄灭的瞬间。
“不……不可能……” 他喉咙里发出嗬嗬、如同破风箱般的声音,带着一种濒死的嘶哑。
他踉跄着后退一步,撞翻了身后一名侍从端着的酒壶,琥珀色的液

毁容后敌国太子把我宠上天沈清秋萧烬大结局
推荐指数:10分
《毁容后敌国太子把我宠上天沈清秋萧烬大结局》主角沈清秋萧烬,是小说写手“如遇星辰”所写。精彩内容:1 刻骨铭心我穿成古代将军的糟糠妻那晚,他正在我脸上刻字。“记住你的身份,沈清秋。”刀尖混着血珠滴落喜被。后来敌国太子为我覆上金面具:“姑娘的眼睛,比草原的星星更亮。”两国和谈宴上,前夫掀翻桌案:“还我夫人!”太子搂紧我的腰轻笑:“萧将军认错人了。”他忽然拔剑指向我颈间疤痕:“这刀痕是我亲手刻的!”......
第1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