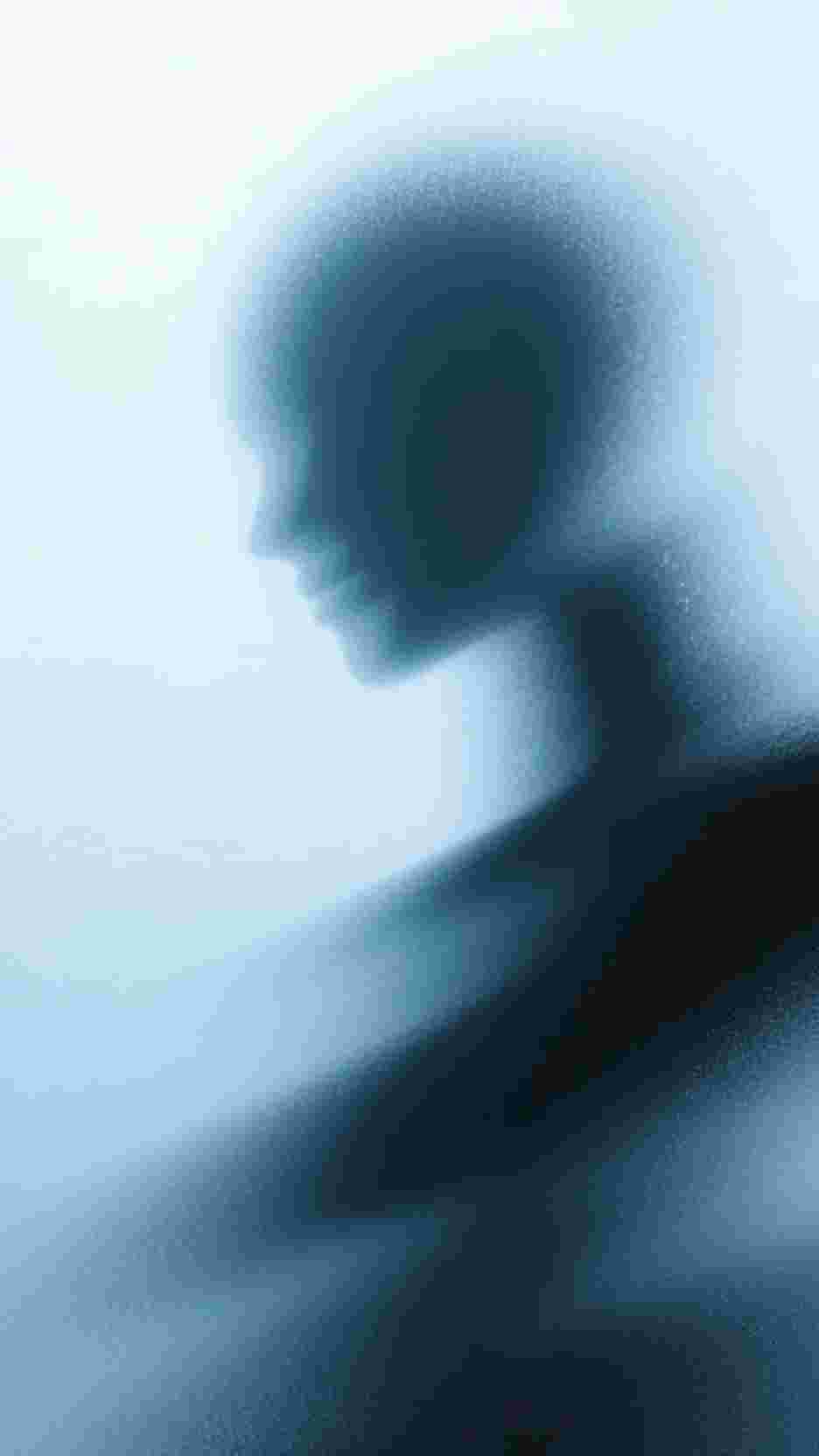时的刀疤,手里拎着的药箱里,装着最新的儿童版格列宁——专门给病友的孩子研发的。
阿明的母亲坐在轮椅上,正在窗口领药。
她的排异反应已经好转,握着林城的手说:“阿明那孩子,用自己换了我们的药……值了。”
阿明因为协助调查被从轻处理,现在在药厂当质量监督员,每天都会在药瓶上贴张便签:“这瓶我试过,放心吃。”
苏晓的报道登在报纸头版,标题用了加粗的黑体:《从“假药”到救命药:一群人的生死突围》。
配图是病友们举着医保单的合影,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红指印——不是按在求情书里,是按在“医保覆盖确认书”上,像一朵朵终于绽放的花。
陈风的手机突然响,是印度药厂的老伙计:“我们新研发的药,想在中国申请上市,你能帮忙吗?”
陈风看着窗外排队领药的人群,笑了:“不用了,我们自己的药,已经够了。”
阳光透过办事大厅的玻璃照进来,在医保单的红章上投下道金光,像给每个名字都镀了层暖色。
林城摸出兜里的旧药瓶,里面的胶囊早就空了,但瓶壁上的指印还在——是陈风的,是病友们的,是所有为活下去拼过命的人,留在这世上的温度。
尾声·药碑霜降那天,抗癌药科普馆开馆。
化工厂的废墟里,三百二十七块药瓶碎片拼成的墙在夕阳下泛着冷光,每块碎片里都嵌着当年的血书残片,红指印透过玻璃,像凝固的火。
陈风站在“陈卫国试药纪念墙”前,父亲的日记复印件被镶在防弹玻璃里。
最后一页的血字洇开:“2015年1月27日,听说儿子被捕,我把提纯剂配方刻在药瓶底——瓶底的凹陷,是留给你们的钥匙。”
他摸出当年的印度药瓶,用激光笔照向瓶底,果然显出行小字:“去仓库地下室,那里有真药的魂。”
地下室的保险箱里,躺着三百支冻干的格列宁原粉,标签上的日期是2013年3月17日——陈风父亲“去世”的日子。
原粉旁边是本实验日志,最后一页画着条曲线,和国产仿制药的疗效曲线完全重合。
阿明推着母亲站在人群后排,老人的化疗疤痕上盖着新长的皮肤。
她攥着阿明的手,指甲掐进他手腕的旧淤青里:“

千条命抵不上一桩罪全文+后续+结局
推荐指数:10分
《千条命抵不上一桩罪全文+后续+结局》是由作者“兔窝窝”创作的火热小说。讲述了:楔子·血书法庭外的台阶被秋雨泡得发涨,三百二十七张血书在风里掀动,红指印洇透纸背,在\...
第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