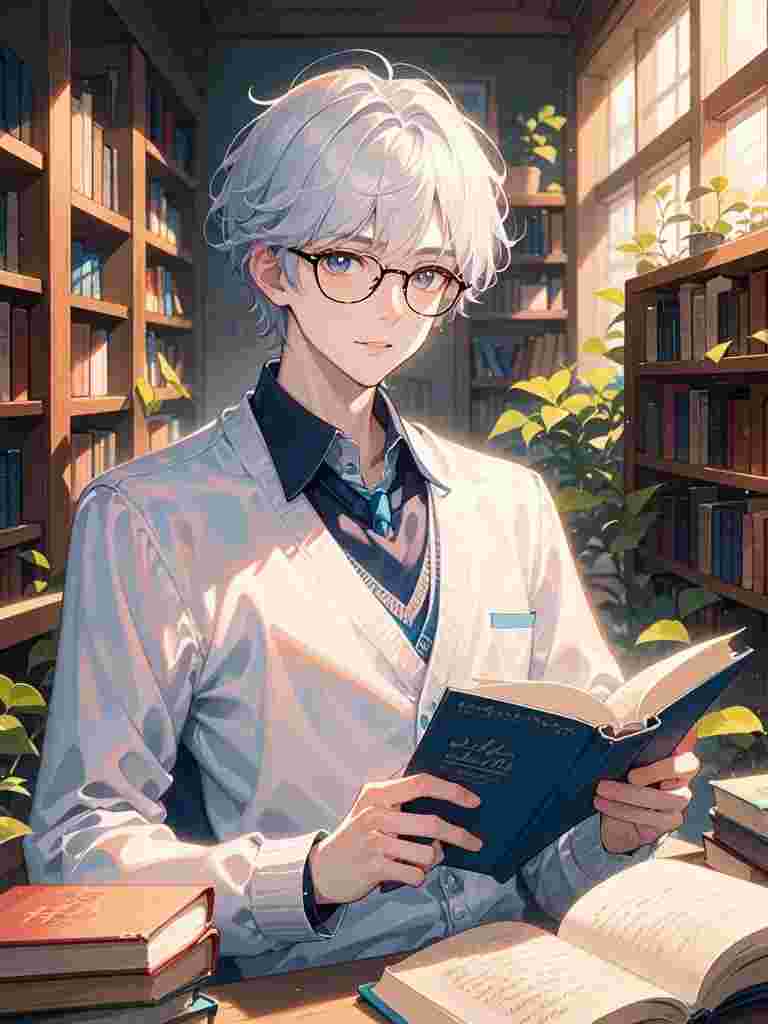在感,起初就像那张纸巾一样单薄。
她是隔壁部门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淹没在格子间的芸芸众生里,毫不起眼。
那时的我,刚从林晚那场烈火中逃生,身心俱疲,对任何形式的“美丽”都心有余悸,甚至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排斥。
苏合的平凡,像一块不起眼的岩石,反而成了我此刻唯一能安心停靠的地方。
最初在一起时,朋友们的眼神里总藏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
他们见过林晚如何光芒四射,再看苏合,那目光里的对比和疑问几乎不加掩饰:“就这?”
连我自己,在最隐秘的角落,也偶尔会掠过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带着优越感的念头:她确实普通。
可这份普通,却滋长出意想不到的安宁。
苏合像一片温润的土壤。
她不会因为我加班错过纪念日而歇斯底里,只会默默留一盏灯和一碗温在灶上的汤。
她的关心细碎而实在,天冷加衣,出门带伞,抽屉里永远有备好的常用药。
她的情绪稳定得如同老树的年轮,没有惊涛骇浪,只有日复一日的温煦平和。
这种安稳,对于刚从惊涛骇浪中靠岸的我来说,简直是沙漠中的甘泉。
我伸出手,握住苏合放在我肩头的手。
她的手心温暖而干燥,带着药油的微黏。
水流在我们之间轻轻晃动,水汽氤氲中,她平凡的面容显得柔和而真实。
一种巨大的、劫后余生般的庆幸感,伴随着温泉水暖,丝丝缕缕地渗透进四肢百骸。
这感觉如此实在,如此熨帖,几乎让我确信,命运终于垂怜,给了我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一次平静呼吸的权利。
“真好。”
我低声说,更像是对自己喟叹。
苏合只是温顺地笑了笑,没有追问,手指又轻轻按揉了几下那道旧疤,仿佛要彻底抚平它,也抚平它所连接的那段过往。
水汽愈发浓重,几乎像乳白色的绸缎,沉甸甸地悬浮在温泉池上方。
廊下昏黄的灯光穿透进来,光线被水雾折射、扭曲,光怪陆离地投在木质池壁和我们的脸上。
就在这片暖融的静谧几乎要凝固成永恒的时刻,一个清朗、略带金石之音的笑声,毫无预兆地穿透了浓稠的水雾,打破了这方小天地里刻意营造的安宁。
“哈哈哈!
妙极!
妙极!”
笑声由远及近,带着一种不合

当债主为我挡刀,恩人递来毒茶番外+无删减版
推荐指数:10分
小说叫做《当债主为我挡刀,恩人递来毒茶番外+无删减版》是“优雅剑侠”的小说。内容精选:蜜月旅行的第一夜,温泉酒店的水汽蒸腾着爬上木质窗格,模糊了外面山林的墨色轮廓。我仰靠在池壁,温泉水温柔地包裹上来,水流如同细密的抚慰,轻轻熨帖着疲惫的肌肉,也仿佛温柔地舔舐着我身上那些早已褪色的、被遗忘的旧伤痕。苏合坐在池边,微俯着身子,纤细的手指正沾了某种淡青色的药油,小心涂抹在我肩胛骨一道浅淡的......
第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