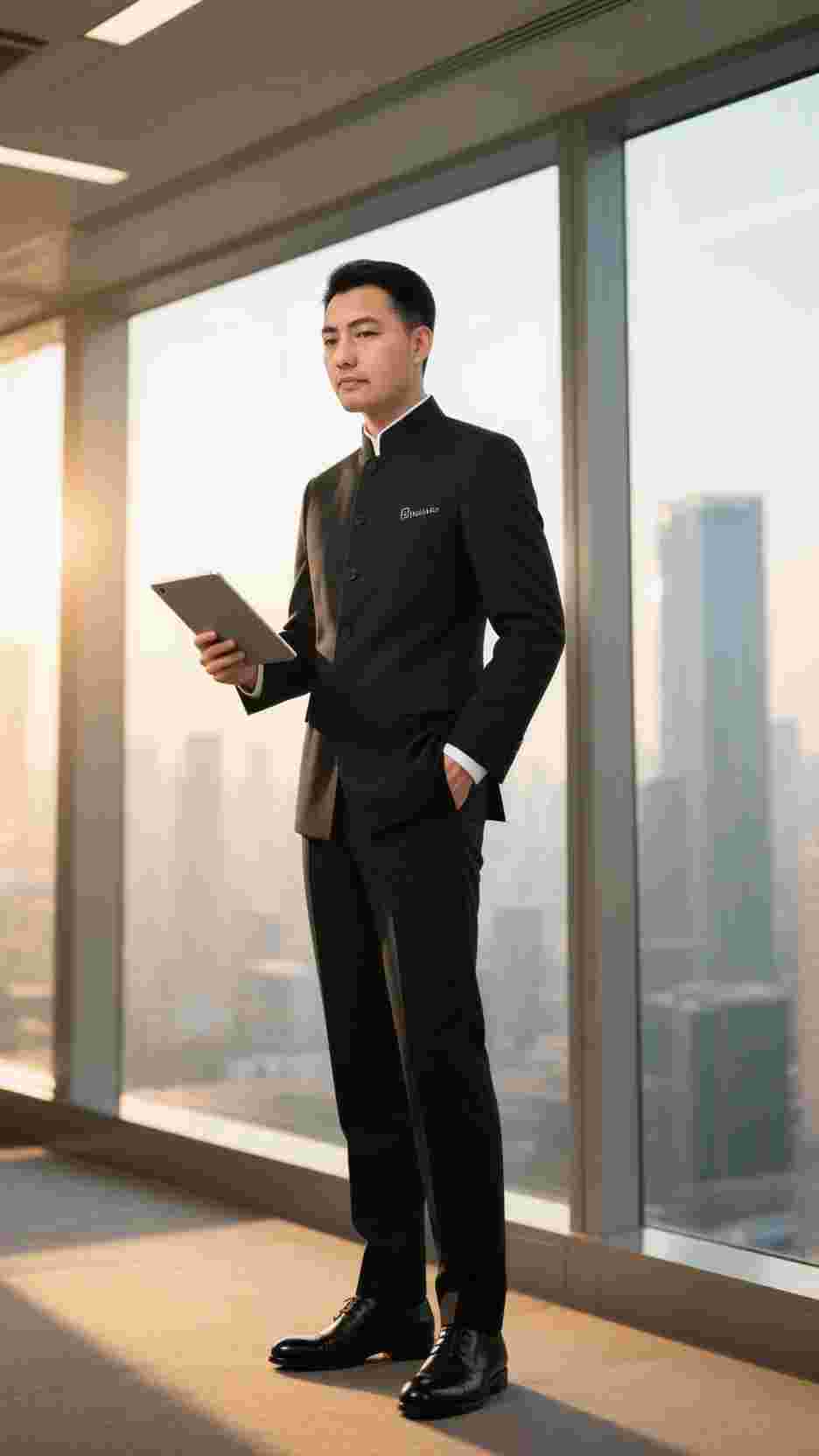的侧脸,兄弟们的背影,后山的野菊,还有那座开满鲜花的山谷——只是这一次,山谷里的花不再带着血腥,而是闪着温暖的光。
张峰偶尔会发信息来,说研究所还在研究时空褶皱,但他已经不负责这个案子了。
“昨天看到你发的画了,”他说,“比当年的素描进步多了。”
我笑着回复:“因为现在的画笔,握着两个人的力气。”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里,我又回到了那座山谷。
二十年前的自己站在花海中央,没有蒙面,笑着冲我挥手。
我走上前,想对他说些什么,他却抢先开口:“你看,花开得多好。”
是啊,花开得多好。
那些被埋葬的青春,那些被辜负的时光,那些以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其实都在时光的土壤里,悄悄发了芽。
而我,终于学会了带着它们,继续走下去。
窗外的月光落在画架上,照亮了未完成的画布。
上面画着一座山谷,山谷里开满了花,花冢上,有一株新芽正迎着阳光,努力生长。
9 画笔里的新生画室的窗总是开着的,风带着楼下银杏叶的气息溜进来,吹动画纸上未干的油彩。
我开始规律地画画,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画布上渐渐堆满了故事——有温哥华咖啡馆里那杯没喝完的拿铁,有烧烤摊升腾的烟火气,有兄弟们在后山步道上拉长的影子,还有林小满当年最喜欢的、开得泼泼洒洒的野菊。
周明常来画室坐坐,他不打扰我动笔,只是坐在角落翻书,偶尔抬头看看画布,轻声说:“这里的光影,像极了大学图书馆的午后。”
我知道他说的是哪段时光。
那时我们总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待一下午,他读诗,我画画,阳光把书页和画纸都晒得暖洋洋的。
原来那些被我刻意尘封的日子,细节从未模糊,只是需要一支画笔来唤醒。
这天,我正在画一幅《山谷》。
画面中央不再是孤零零的坟茔,而是一片蓬勃的花海,花海深处站着两个身影——一个是穿着风衣的“现在的我”,一个是穿着白衬衫的“二十年前的我”,他们并肩望着远方,像是在对话。
画笔顿在半空时,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是我老家的小城。
“请问是陈默先生吗?”
电话那头是个苍
小说《青春之冢》试读结束,继续阅读请看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