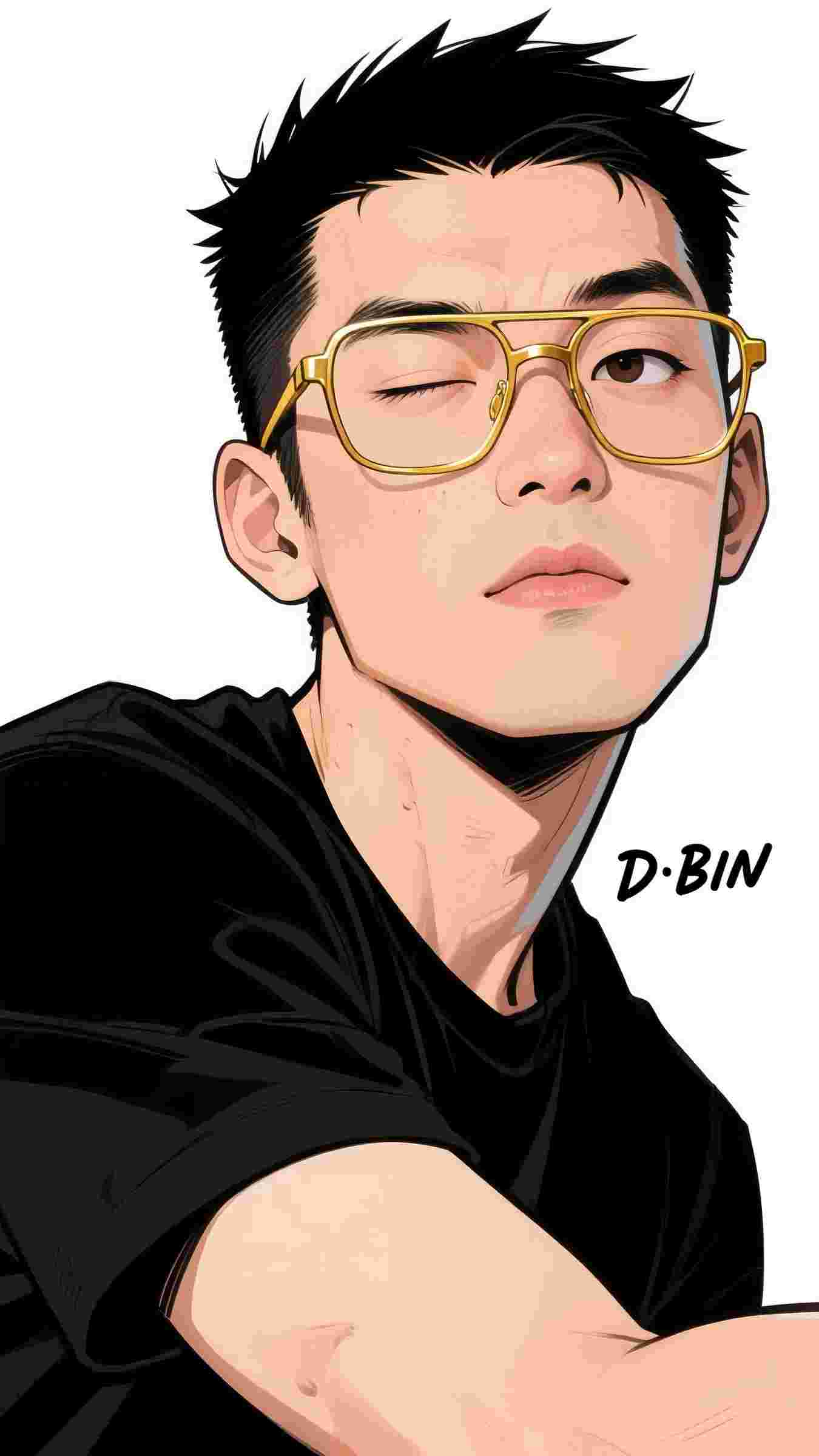花纹的橡木大门。
外面,南城初冬的夜风,裹挟着湿冷的寒意,像无数把细小的冰刀,瞬间割在脸上。
别墅区精心打理过的道路在惨白的路灯下延伸,两旁是沉默的、修剪整齐的昂贵绿植,投下浓重而压抑的阴影。
身后,那座灯火通明、如同巨大水晶盒子的许家别墅,像一个冰冷华丽的坟墓,隔绝了所有的暖意。
我一步踏了出去。
高跟鞋踩在冰冷的柏油路面上,发出清晰的“咔哒”声。
没有回头。
一步,又一步。
身后的喧嚣、灯光、那令人作呕的暖香,被冰冷的夜风迅速吹散、拉远。
风卷起我湿透的裙摆,紧贴在腿上,冷得像冰。
走了不知多久,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半小时。
意识开始变得模糊,视野边缘像被泼了墨汁,一点点暗下去。
身体的力气被彻底抽空,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又沉又软。
心脏在胸腔里不规则地、沉重地搏动着,每一次跳动都牵扯着难以忍受的闷痛。
终于,在一条远离别墅区的、昏暗僻静的小巷转角,眼前骤然一黑。
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栽倒,额头重重磕在冰冷粗糙的墙壁上,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
剧痛袭来,却不及心口万分之一。
世界彻底陷入无边无际的、冰冷的黑暗。
意识在粘稠的黑暗中沉沉浮浮,像溺水的人。
刺鼻的消毒水气味顽固地钻入鼻腔,冰冷而熟悉。
耳边似乎有模糊的、遥远的交谈声,断断续续,如同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
“……真是可怜……许家那位‘假千金’…………听说被赶出来时,她弟弟直接把人行李扔喷泉池里了…………啧啧,豪门啊,翻脸比翻书还快…………不过也怪她自己,鸠占鹊巢十八年……鸠占鹊巢”……又是这个词。
像一根生锈的针,狠狠扎进混沌的意识里,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
我努力地想睁开眼,眼皮却沉重得像被焊死。
身体仿佛被碾过,每一块骨头都在叫嚣着疼痛,尤其是额头,传来一阵阵钝痛。
不知过了多久,那层隔膜似乎变薄了些。
交谈声变得清晰了一点,是两个年轻女声,带着点疲惫的慵懒和……某种隐秘的兴奋?
“……哎,你说那报告是真的假的?”
一个声音压得更低了些,带着点八卦

被弃假千金?我才是真血包许知微许崇山全文+结局+番外
推荐指数:10分
最具潜力佳作《被弃假千金?我才是真血包许知微许崇山全文+结局+番外》,赶紧阅读不要错过好文!主人公的名字为许知微许崇山,也是实力作者“无蔗糖兔子”精心编写完成的,故事无删减版本简述:香槟塔在巨型水晶吊灯下折射出迷离的光晕,气泡细小而急促地向上翻涌,像一场无声的狂欢。空气里浮动昂贵的香水、雪茄和刚摘下的白玫瑰甜腻混合的香气,熏得人有些恍惚。我,许知微,穿着巴黎空运来的当季高定礼服裙,裙摆缀着细碎的钻石,随着脚步在光滑如镜的大理石地面上划过细微的沙沙声。今天是我十八岁的生日宴,整个......
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