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绾卿。”她站直身子,目光比青州的井水还凉,“是沈凝的女儿。”
族长的拐杖“咚”地戳在地上,震起些尘土:“沈凝?她早就死在外面了!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哪配进沈氏祖坟?”
石砚之上前一步,将沈知意护在身后:“族长说话未免太难听。阿凝与先父情投意合,是苏洪强抢民女,害了她一生。”
“强抢?”族长冷笑起来,拐杖在掌心转了个圈,“她爹欠苏洪三百两赌债,用女儿抵债天经地义!倒是你们石家,当年若肯拿出银子帮沈家还债,何至于落到今天?”
红绳突然缠上他的拐杖,沈知意眼前炸开一片血色——族长把生母的求救信塞进灶膛,苏员外站在一旁递过个沉甸甸的钱袋:“只要你咬死沈凝是自愿嫁我,这银子就是你的。”
“所以你就眼睁睁看着我娘被抢走?”沈知意的声音发颤,红绳勒得手腕生疼,“甚至帮着苏洪掩盖她被毒杀的真相?”
族长的脸色瞬间白了,拐杖差点脱手:“你……你胡说什么!”
“我是不是胡说,去枯井里看看便知。”沈知意指向后院,红绳映出的虚影里,族长正指挥家丁往井里扔石头,井底隐约传来女人的呜咽,“我娘被苏洪毒杀后,是你亲手把她的尸骨埋进沈家祖坟,就为了苏家每年给的那点好处!”
“放肆!”族长大怒,拐杖朝沈知意挥来,却被石砚之伸手挡住。铜箍撞在石砚之的骨头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红绳突然亮起红光,将两人弹开数步。
“沈族长,”石砚之的声音冷得像冰,“二十年前你收苏家银子的账本,我们已经找到了。若不想闹到官府去,就把当年的事说清楚。”
族长的嘴唇哆嗦着,突然瘫坐在地,拐杖滚到沈知意脚边。红绳触碰拐杖的刹那,无数画面涌来——他偷偷给生母送过药,却被苏员外发现打得半死;他在苏府墙外徘徊,听见生母被毒打却不敢进去;他把生母的银簪藏在井台缝里,盼着有朝一日能物归原主。
“我也是没办法啊……”族长捂着脸哭了起来,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沈家那时快败光了,族里几十口人等着吃饭……苏洪说只要我帮他,就给沈家修祠堂、买良田……”
沈知意看着他佝偻的背影,红绳传来一阵复杂的情绪——有恨,有怨,还有丝说不清的怜悯。这世间的恶,往往藏在无奈的外衣下,却终究是恶。
“我娘临终前,让你做过什么?”她捡起地上的拐杖,红绳在杖头绕了个圈,“那支银簪,是她托你交给石伯父的吧?”
族长猛地抬头,眼里满是震惊:“你怎么知道……”他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里面是封泛黄的信,“她让我等石砚之回来,把这个给他,说里面有太子党羽拐卖人口的证据……可我怕苏洪报复,一直没敢……”
沈知意展开信纸,生母的字迹娟秀却有力,写着太子心腹赵衡在青州用“典妻”名义拐卖女子的事,还画了张太守府密道的草图。红绳突然发烫,映出赵衡年轻时的模样,正指挥人把个哭哭啼啼的女子塞进马车,车帘上绣着朵石榴花。
“赵衡……”石砚之的眉头拧成个疙瘩,“青州太守就叫赵衡。”
族长叹了口气,从袖袋里摸出把铜钥匙:“沈氏祠堂的地窖里,还有些当年被拐女子的名册,是你娘偷偷记下来的。她说总有一天,要让这些冤屈见天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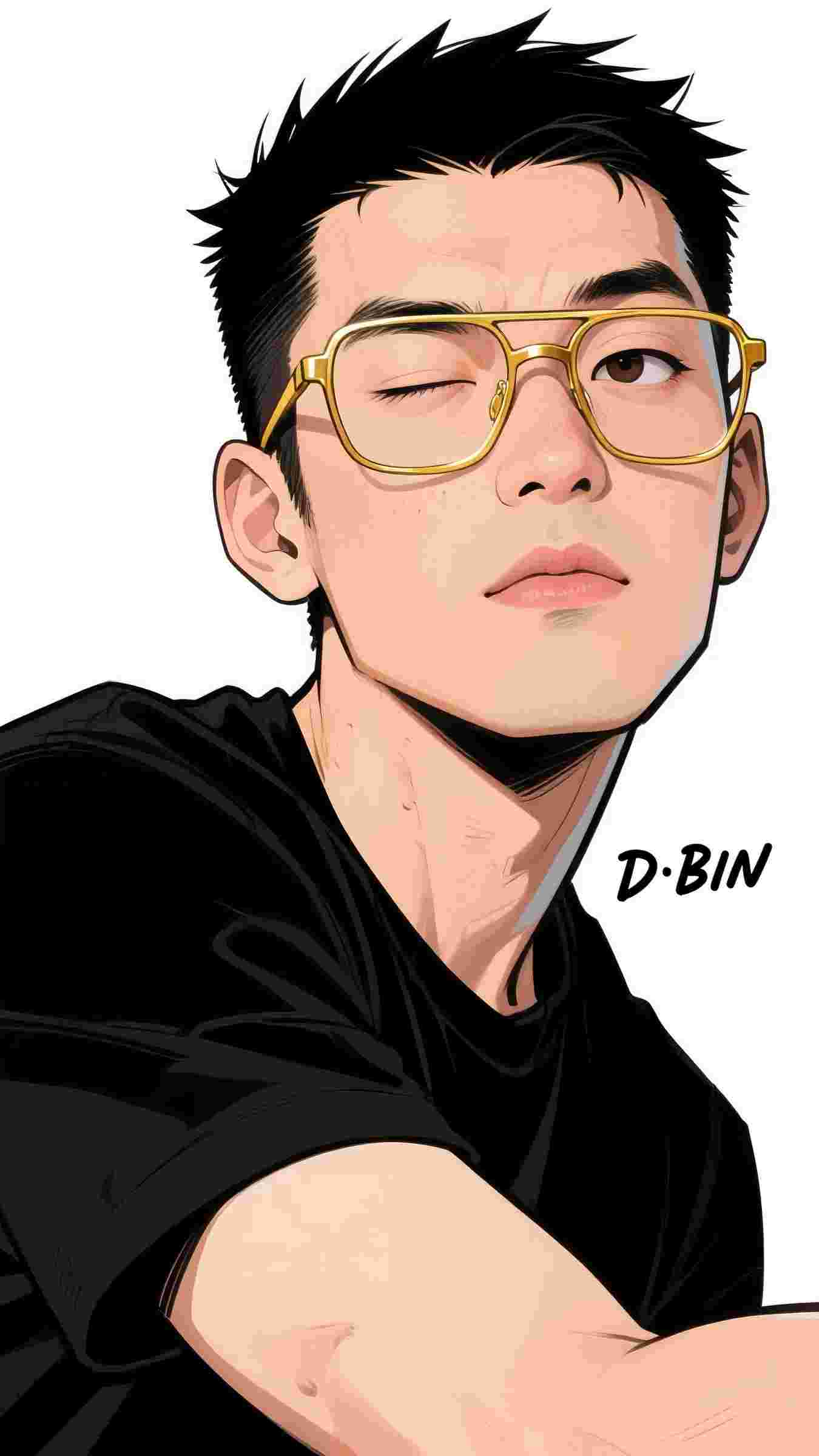
知意绾心无删减全文
推荐指数:10分
最具实力派作家“南柯一梦会卿卿”又一新作《知意绾心无删减全文》,受到广大书友的一致好评,该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沈知意石砚之,小说简介:现代女子沈知意含恨而死时,腕间那道被拐时勒出的红痕,竟成了跨越生死的缠命绳。一睁眼,她成了永宁王朝被父亲典给乡绅冲喜的庶女苏绾卿。雪夜马车上,前世被拐卖的血色记忆与今生抵债的屈辱重叠,红绳发烫,映出乡绅管家与当年拐子重合的阴鸷嘴脸——命运的枷锁,竟以另一种方式缠上了她。装疯避祸的石家少爷石砚之,是第一个能看见她腕间红绳的人。那句“勒得疼吗”,让两个被命运遗弃的灵魂猝然相撞。他要查父亲坠崖真相,她要挣脱任人摆布的宿命,红绳牵引着他们结成同盟,却在逃亡路上窥见更惊人的秘密:石家买过的“病逝”女子、太子与太守的肮脏交易、甚至她生母之死,都与一张拐卖网络息息相关。从乡绅别院到京华风云,从青州秘辛到京城兵变,红绳的力量愈发强大,不仅能回溯过往、预警危险,更将两世的恩怨情仇紧紧缠绕。当太子以人质要挟,当红绳映出他推人坠崖、指使拐卖的全部罪证,沈知意终于明白:困住人的从不是绳索,是不敢挣脱的心。两世纠葛,一场救赎。她带着前世记忆逆袭,他藏着皇子身份守护,缠命红绳的尽头,是罪恶昭彰,是锦绣重生,更是两颗心跨越生死的紧紧相系。...
第39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