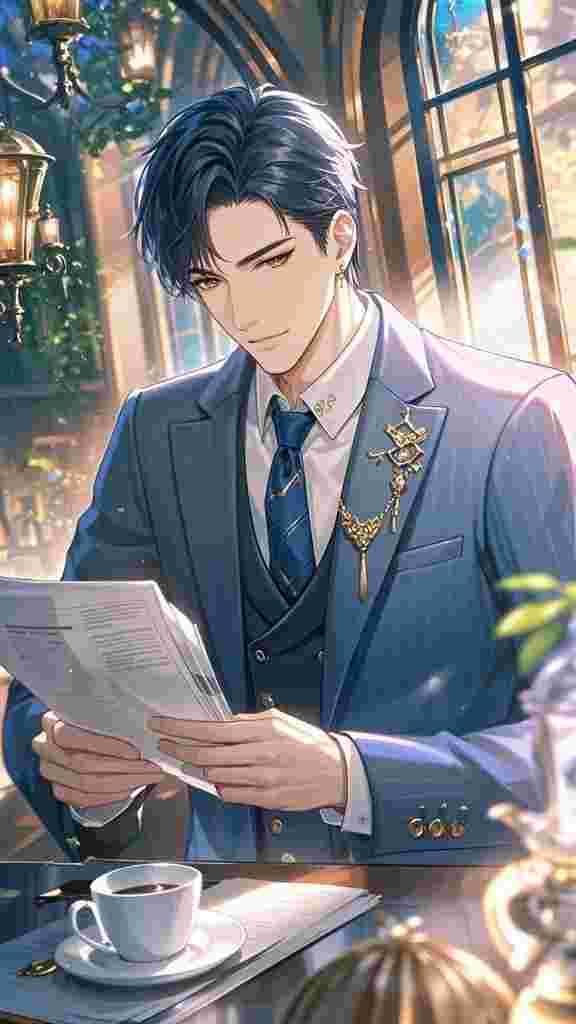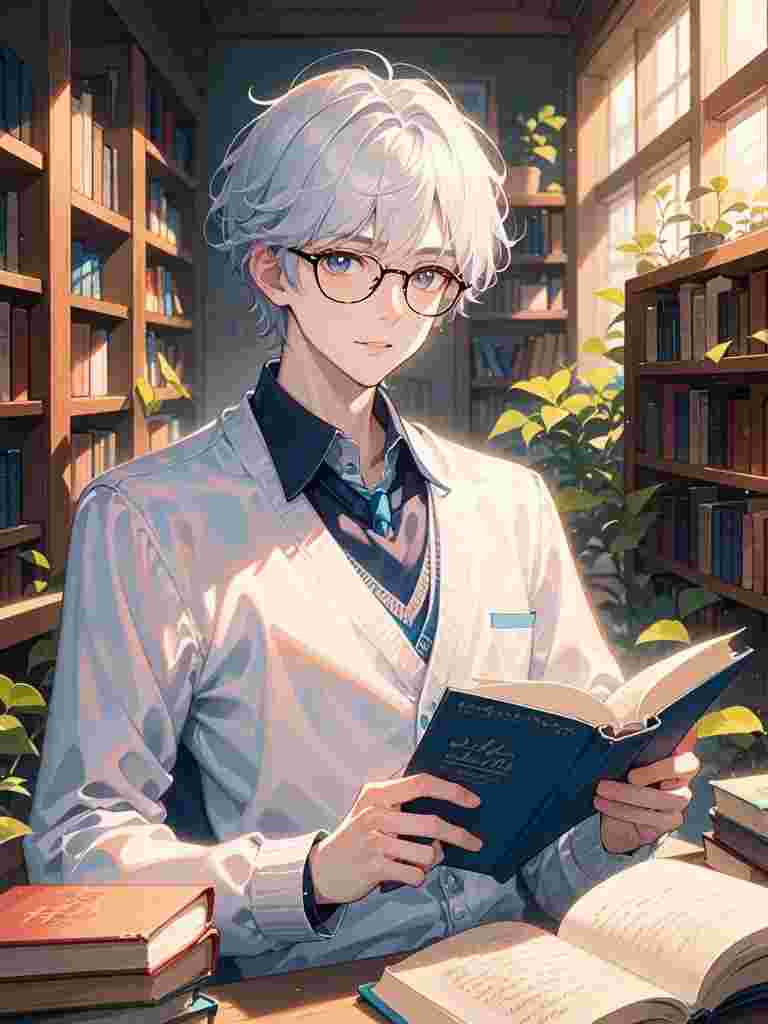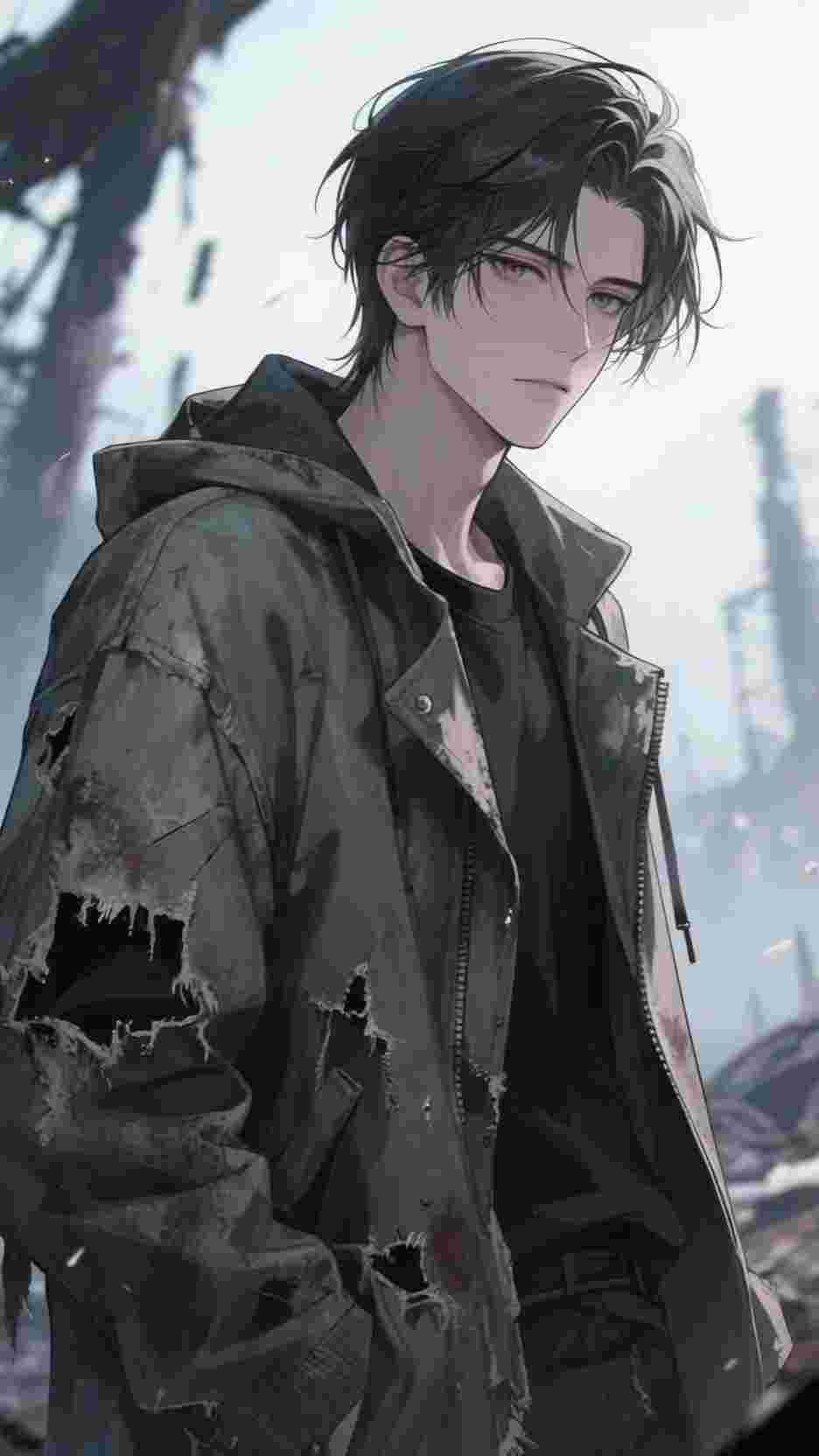“这页被撕了。”按察使叹道,“王记粮行从三年前就开始做假账,张尚书在背后撑腰,谁也查不动。”
江砚指尖划过空白页,忽然道:“大人,能否借‘赈灾库’一用?”
按察使一愣:“赈灾库早就空了,户部拨的粮只够摆样子。”
“空的正好。”江砚笑了,“请大人明日贴出告示,就说朝廷要‘以工代赈’——百姓帮赈灾库修缮粮仓,每日发两斤米。”
按察使眼睛一亮:“这法子好!既给了百姓活路,又能名正言顺地动用工匠,只是……米从哪来?”
江砚往窗外瞥了一眼,月光正照在王记粮行的飞檐上:“米,自然有人‘送’来。”
次日清晨,“以工代赈”的告示贴满了池州城。百姓们围在告示前,指着“每日两斤米”的字样议论纷纷,眼里的绝望渐渐生出些光亮。
“真的假的?”一个瘸腿的老农摸着告示上的墨迹,“朝廷会有这么好的心?”
“按察使大人盖了印的!”识字的书生喊道,“说是京城来的江编修出的主意,让咱们去修赈灾库!”
消息传到王记粮行时,王老板正在给张诚写密信。他把信纸揉成一团,啐道:“修粮仓?我看他是想打我粮囤的主意!”
蒙面人凑过来:“老板,要不要……”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王老板摇摇头:“这姓江的是朝廷命官,明着动他麻烦。你去告诉城西的‘囤粮窟’,加派一倍人手,一只老鼠也别放进去。”
他没注意到,送信的伙计转身时,袖角沾了片槐树叶——那是江砚让老农给的记号,暗示“囤粮窟”的布防已变。
三日后,赈灾库外。
几百个百姓拿着锄头铁锹,热火朝天地修缮粮仓。江砚穿着青衫,站在晒谷场上,亲自给百姓发米。按察使在一旁记账,看着领米的百姓越来越多,眉头却越皱越紧:“江编修,咱们的存粮只够撑五日了。”
江砚往城西的方向看了一眼,那里的炊烟比往日少了许多——他让老农带着几十个“苦主”,每日在囤粮窟外哭嚎,说家里快饿死孩子了,故意搅得守粮的打手心烦意乱。
“再等等。”江砚递给按察使一张纸条,“今晚劳烦大人,让人把这个贴遍全城。”
纸条上写着:“王记粮行暗通外敌,将赈灾粮运往蛮族,证据藏于囤粮窟第三号粮囤。”
按察使一惊:“这……没有实证,怕是会引火烧身!”
“要的就是引火。”江砚压低声音,“张诚的人最怕‘通敌’二字,定会连夜转移粮囤里的东西,咱们正好‘截胡’。”
入夜,三更。
囤粮窟里果然乱了起来。打手们举着火把,手忙脚乱地搬着第三号粮囤的东西——里面哪是什么通敌证据,全是王记粮行与知府的勾结账本。王老板站在粮囤边,亲自监督搬运,额头上的冷汗打湿了绸衫。
“快!把账本烧了!”他嘶声喊道,忽然听到栅栏外传来呐喊声——是按察使带着衙役来了!
“奉旨查抄囤粮窟!”按察使举着江砚给的“便宜行事”手谕,衙役们撞开栅栏,与打手们混战起来。
混乱中,江砚像道青影窜进粮囤,指尖在账本上飞快一翻,将“永乐三年,转运永宁城粮草三千石”那一页撕下,塞进袖中。这才是他真正要找的——永宁城的粮草,果然通过王记粮行流入了私库。
“抓住那个穿青衫的!”王老板看到江砚,红着眼扑过来,手里的短刀直刺他后心。
江砚侧身避开,脚尖勾起一个粮袋,“哗啦”一声,米袋砸在王老板脚下,他脚下一滑,短刀脱手飞出,正好扎在粮囤的帆布上。

影阁主,从丫鬟养子到天下执棋人江离沈月:全章+后续
推荐指数:10分
古代言情《影阁主,从丫鬟养子到天下执棋人江离沈月:全章+后续》目前已经全面完结,江离沈月之间的故事十分好看,作者“锦文大大”创作的主要内容有:在以“内息淬体”为修炼基础、势力纷杂的玄幻世界,青阳城江家三少爷江离,看似玩世不恭,实则暗藏谋略。他周旋于大乾王朝、王府、光明神殿、影阁等各方势力间,借金符之事搅乱棋局,又在与神秘女子沈月、影阁鼠儿等交互中,探寻各方隐秘。江离带着妹妹江仪,一路历经沼泽遇腐骨鳄、城池中明暗势力交锋、神秘纸条与影阁密令等事件,逐步揭开世界的复杂脉络,从青阳城走向京城,而京城更大的风暴与秘密,正等待他去直面,一场关乎命运、势力博弈与真相探寻的冒险,在玄幻江湖中徐徐展开 ……...
第3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