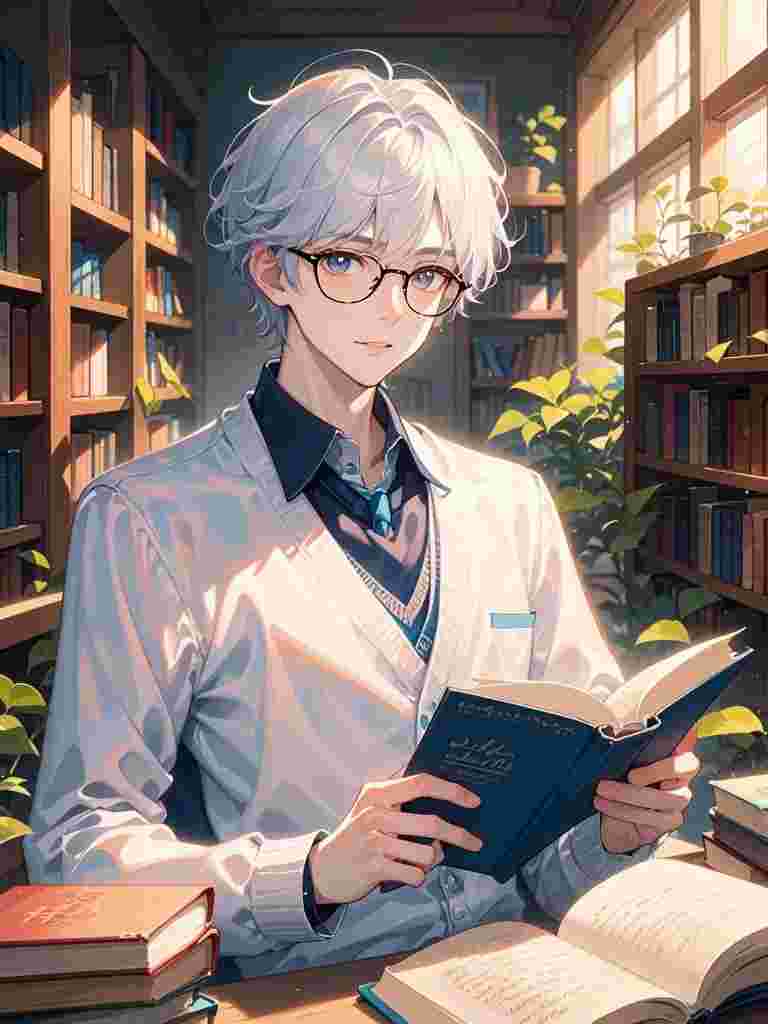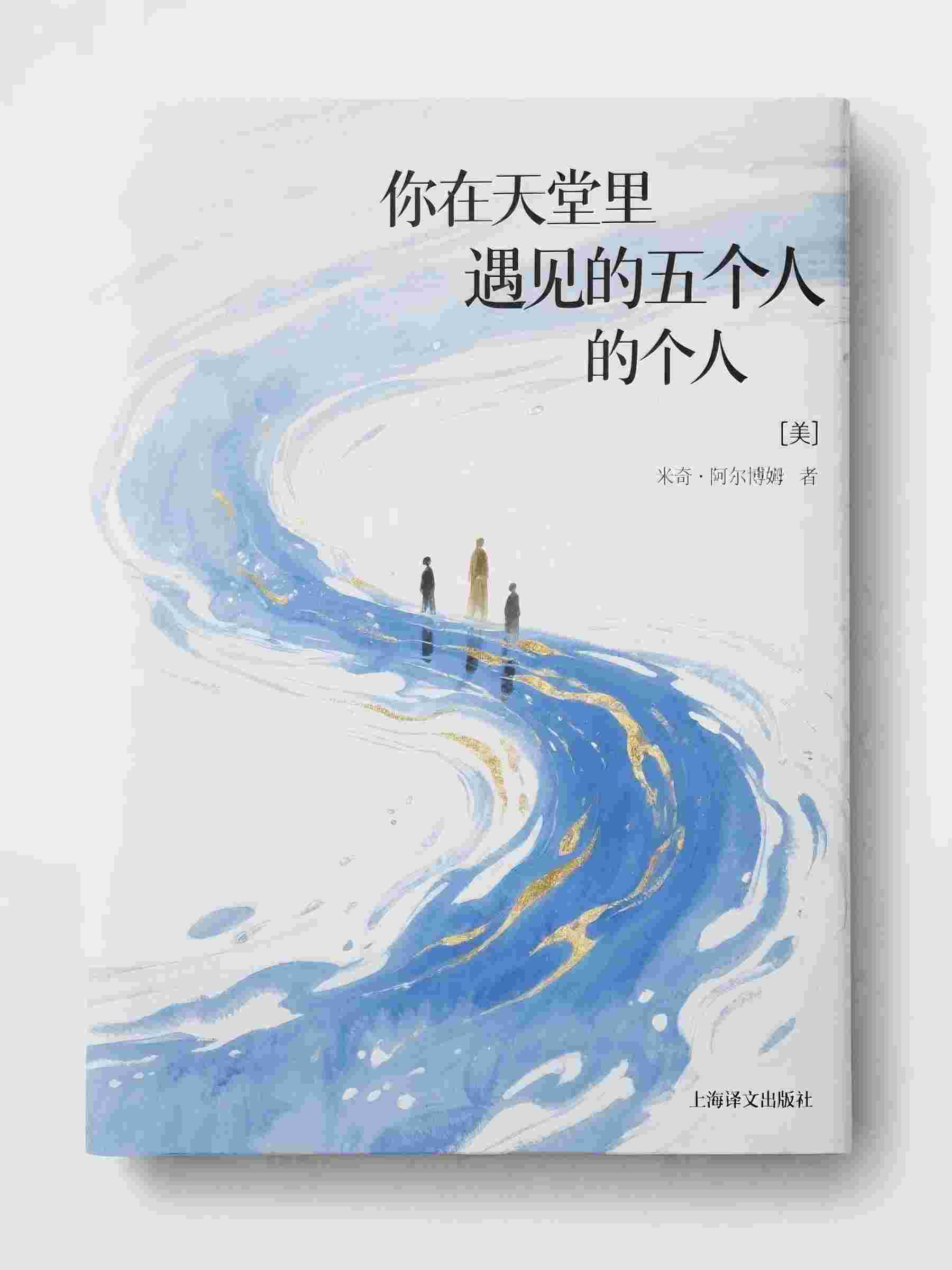小世子季临的生辰宴近在眼前,整个将军府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桑景宜坐在铜镜前,望着镜中憔悴的自己,指尖轻轻抚过眼下的青黑。
“夫人,今日是小世子的生辰宴,您……”
丫鬟欲言又止,“您总不能穿得太过素净。”
桑景宜垂眸,看着自己仅剩的几件旧衣,不是洗得发白,就是缝补过的痕迹。
她如今双腿残疾,又被禁足偏院,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
“现在定做,怕是来不及了……”她轻叹一声。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姐姐可在?”
苏明月笑盈盈地走进来,身后跟着两个丫鬟,手里捧着一个精致的锦盒。
“姐姐,明日是临儿的生辰宴,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件礼服,你看看可还喜欢?”
桑景宜抬眸,警惕地看着她。
“怎么,姐姐不信我?”苏明月故作委屈,“我只是想着姐姐如今行动不便,怕你来不及准备……”
桑景宜抿了抿唇,伸手接过锦盒。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件湖蓝色的云锦长裙,绣着精致的暗纹,华贵却不张扬。
她仔细检查了一番,并未发现任何不妥。
“多谢。”她低声道。
苏明月掩唇一笑:“姐姐喜欢就好,明日宴会,可要打扮得漂亮些。”
说罢,她转身离去,背影婀娜。
桑景宜望着那件衣裳,心中仍有疑虑,可眼下确实别无选择。
……
翌日,宴会开始前,桑景宜换上了那件湖蓝色长裙。
镜中的女子虽面容憔悴,可这身衣裳却衬得她气质清冷,宛如出水芙蓉。
丫鬟扶着她坐上轮椅,推着她缓缓前往正厅。
一路上,下人们纷纷侧目,眼中闪过惊艳之色。
可当她被推入正厅的那一刻——
原本喧闹的宴会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她身上,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桑景宜心头一颤,隐隐察觉到了不对劲。
她抬眸,正对上季淮书冰冷的目光。
他的眼神里带着滔天的怒意,仿佛要将她生吞活剥。
“桑、景、宜。”他一字一顿,声音森寒得令人毛骨悚然。
桑景宜手指微微发抖:“将军……”
“来人!”季淮书猛地站起身,“把她身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桑景宜瞳孔骤缩,还未反应过来,两个粗使婆子已经冲上前,粗暴地拽住她的衣领。
“不!你们做什么!”
她拼命挣扎,可双腿残疾的她根本无力反抗。
“刺啦——”
衣料撕裂的声音在寂静的厅内格外刺耳。
她的外衫被撕开,露出里面单薄的里衣。
“住手!放开我!”
她羞愤交加,泪水夺眶而出。
就在这时,一位雍容华贵的老妇人疾步走到她面前,扬手狠狠给了她一耳光!
“啪!”
清脆的巴掌声响彻大厅。
桑景宜被打得偏过头,脸颊火辣辣地疼。
“贱人!你怎么敢穿我女儿的衣服!”
老妇人声音颤抖,带着哭腔,“我苦命的女儿连穿都没穿过就去了啊!”
桑景宜浑身一僵,不可置信地抬头。
这件衣服……
是季淮书亡妻的遗物?
她猛地转头看向苏明月。
“不是我!是苏明月拿给我的!她说这是为我准备的礼服!”
“姐姐,你怎能如此污蔑我?”
苏明月泪如雨下,“谁不知道我与姐姐姐妹情深,我怎会用她的旧衣来害你?”
“老夫人,我发誓真的不知这是令爱的衣裳……”桑景宜颤抖着伸手想整理被撕破的衣料,“我这就将它好好补——”
“啪!”
又一记耳光重重甩在她脸上,老妇人目眦欲裂:“你这贱妇也配碰我女儿的衣裳?!”
桑景宜嘴角渗出血丝,耳边嗡嗡作响。
她看见季淮书起身走来,玄色锦袍在烛光下泛着冰冷的光泽。
“季将军!”老妇人突然转身跪下,“这毒妇如此折辱亡女,老身求将军做主啊!”
季淮书扶起老夫人,转头看向桑景宜的眼神像在看什么肮脏的东西。
“来人,把她拖到街上,让全京城都看看,将军府的主母是个什么货色。”
“不!”桑景宜挣扎着抓住轮椅扶手,“将军开恩!妾身真的不知……”
粗粝的麻绳已经勒进她手腕。
侍卫粗暴地将她拖下轮椅,钗环散落一地。
中衣在拉扯间裂开道口子,露出大片苍白的肌肤。
“淮书哥哥。”苏明月突然轻扯季淮书衣袖,“姐姐毕竟是主母,这样是否……”
“你总是心软。”季淮书捏了捏她的手,“可有些人,不配得到怜悯。”
初春的夜风刀子般刮过肌肤。
桑景宜被铁链锁着脖颈,像牲畜般拖行在青石板上。
“快看!那就是欺负将军亡妻的毒妇!”
铜锣声惊醒了整条街巷,无数窗户接连亮起灯火。
侍卫高声宣扬着她的“罪状”,说她在亡妻忌日穿其遗物招摇过市。
“当年苏夫人给我们施粥的恩情还没忘呢!”
“打死这个忘恩负义的贱人!”
烂菜叶混着碎石砸来,桑景宜抬手遮挡,一块尖石却正中额角。
温热的鲜血流进眼睛,将整个世界染成血红。
恍惚间她抬头,看见醉仙楼雕花窗前,季淮书正揽着苏明月凭栏而立。
季临趴在栏杆边兴奋地拍手,嘴里喊着“打得好”。

落泪已是照孤影:全文+结局+番外
推荐指数:10分
小说叫做《落泪已是照孤影:全文+结局+番外》是“买麦芽”的小说。内容精选:世人皆道桑景宜命好,嫁了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季淮书。可现在,一个妾室,却颐指气使地要打掉她的孩子。“夫人,你还是乖乖把这碗药喝了吧。”青瓷药碗递到眼前时,桑景宜闻到了藏红花浓烈的腥气。她猛地抬头,正对上苏明月含笑的杏眼。“我不喝!”桑景宜挥袖打翻药碗。此刻,季淮书就坐在三步外的紫檀圈椅上。他修长的手指摩挲着青玉扳指,眼眸冰冷。“将军!”桑景宜扑跪在碎瓷上,月白裙裾瞬间洇出点点红梅。“妾身发誓从未害过小世子,求您不要伤害妾身腹中胎儿……”她拼命磕头,“他绝不会与大公子争什么,妾身可以带着孩子去庄子上……”“姐姐这话说的,倒像我们容不下个婴孩。”...
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