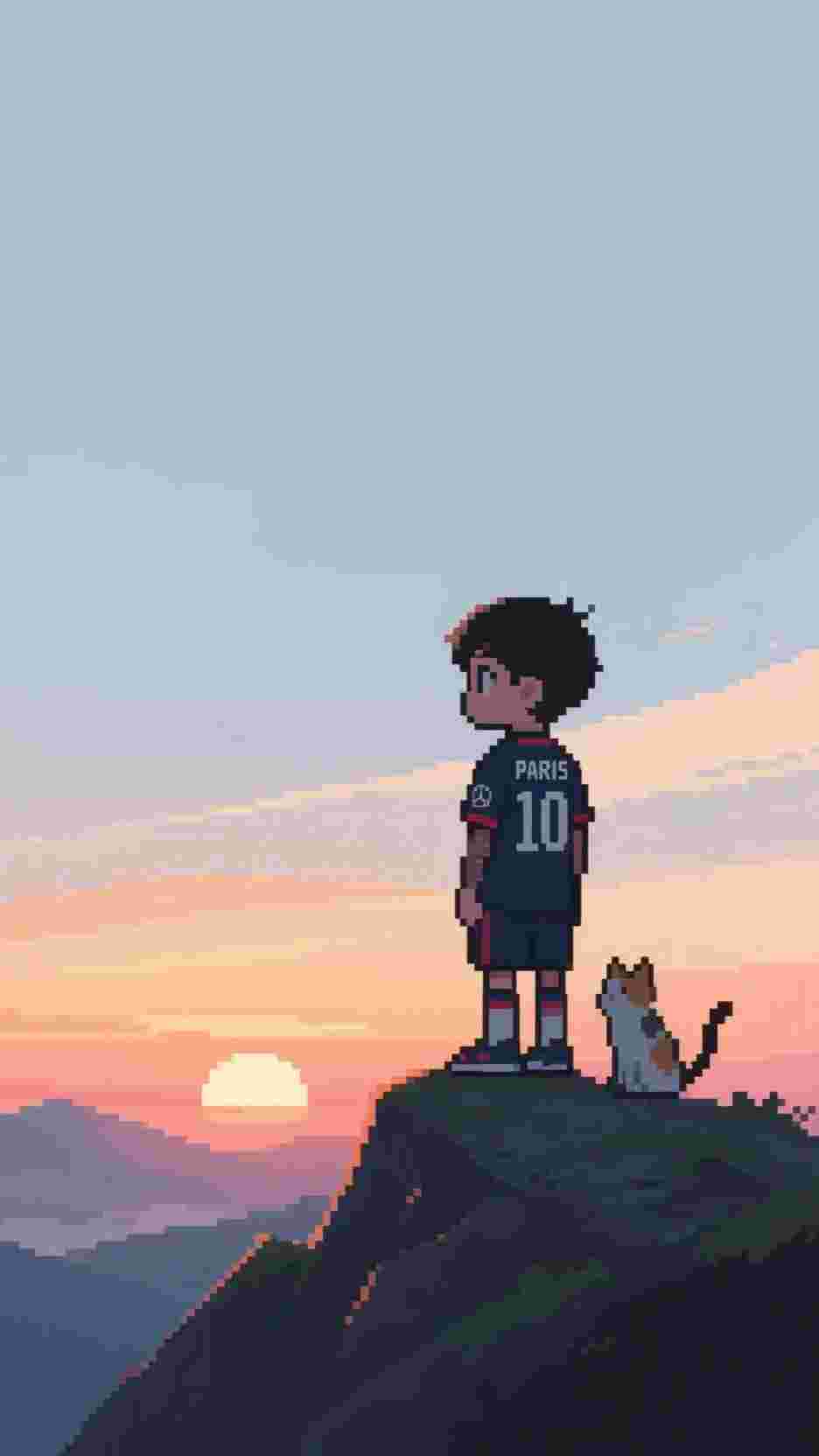钱。
我盯着陈倩倩和秃瓢,嘴唇抖得说不出完整句子:“爱咋咋地。”
见我咬牙切齿,秃瓢哥立马就想上前揪我衣领子。
就在我以为今天得脱层皮时,包房门被敲响,传菜的小哥推门进来上菜,打断了秃瓢哥。
我低着头,趁机冲出包房。
身后传来秃瓢哥的骂声:“草,你给老子等着,扫兴!”
陈倩倩的声音追出来:“谢浓娣,你给我回来!
敢跑,明天就别想上班!”
我没停,一路跑到后巷,蹲在地上狂吐。
胃酸混着啤酒烧得喉咙生疼,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吐完了,我抬头看天,黑得跟锅底一样,一颗星星都没有。
腿肚子火辣辣地疼。
我卷起裤腿,看见小腿鼓起一大片水泡。
后巷灯光昏暗,我把手机电筒打开,照着腿上的伤,心里忽然特别平静。
烫得真好,疼得真好。
再疼,也比被人当玩意儿耍好。
我抹了把脸,站起来,把围裙解下来狠狠扔垃圾桶里。
我来到附近的小诊所,护士小姐姐给我处理伤口说:“你这算工伤吧,得让老板赔钱啊!”
我愣住:还能赔钱?
护士看我像看外星人:劳动法了解一下?
不赔可以报警。
3 火锅店风波我处理完伤口回到地下室,推开生锈的绿漆铁门,一股霉味扑过来,像一床湿棉被闷在脸上。
走廊灯发黄、打颤,也没人换一下。
我的影子贴在墙上,像条弓着背的狗,拉得老长。
屋里比走廊更黑。
上铺的婉芬又偷偷把男朋友带回来了。
两人裹在一床粉色被子下面,被子一起一伏,床板吱呀吱呀,节奏比DJ还稳。
我屏住呼吸,踮脚进去,想把书包先放下,“啪”,书包带碰倒了地上的脸盆,铁盆撞水泥地,“咣”一声巨响。
床板瞬间安静。
婉芬探出半个脑袋,口红糊到下巴,语气比我还尴尬:“浓娣……你、你咋这么早回来?”
我笑笑:“客人临时散了。”
那男的瞥了我一眼,嘀咕一句“扫兴”,翻身朝里。
婉芬压低声音:“那啥,灯给你留着,你轻点哈。”
留灯?
灯管早坏了,只剩床头一盏充电小夜灯,发着肾虚似的蓝光。
我把夜灯拧到最暗,蹲在地上收拾被踩散的英语书。
书页卷边,单词密密麻麻,像一群蚂蚁。
我找到今天该背的list,刚要张嘴·

火锅妹的复仇:从受虐到爽翻赵嫦娥嫦娥:番外+无删减版
推荐指数:10分
现代言情《火锅妹的复仇:从受虐到爽翻赵嫦娥嫦娥:番外+无删减版》,讲述主角赵嫦娥嫦娥的甜蜜故事,作者“确凿”倾心编著中,主要讲述的是:1 晦气女孩我叫谢浓娣,光听这名字就透着一股“晦气”的味道。亲妈生我的时候,爷爷奶奶蹲在产房门口,跟俩门神似的,一听护士说是个女孩便当场拍板:“送人,赶紧送人。得亏亲妈还有点良心,我才勉强没被装进纸箱丢进福利院。可留下归留下,我从此就成了全家人的保姆、出气筒,谁都能上来踹一脚的破皮球。五岁踩着小板凳......
第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