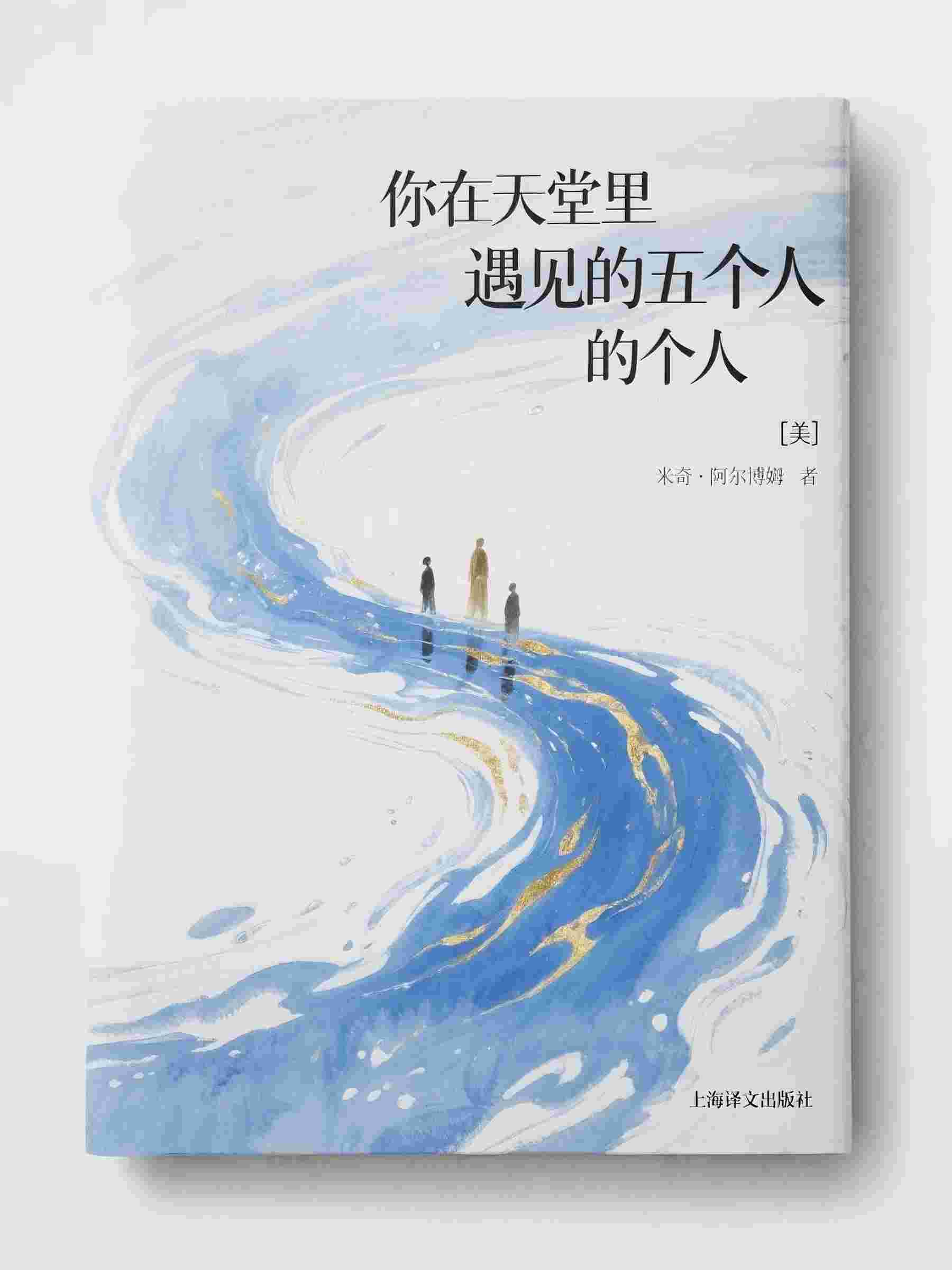衫。
我抹了把脸,抹不净的雨水顺颊而下。
掏出那部边角漆都蹭掉大半的旧手机。
雨水在屏幕上肆意横流。
划开屏幕,点开置顶的那个名字——“卫国”。
指尖在屏幕的凉意里停留一瞬,用力按了下去。
2“嘟——嘟——”长音在雨声背景里显得空洞悠远,每一声都像敲在紧绷的冰弦上。
就在绝望的寒流即将封冻一切前,咔哒一声,电流杂音里传来熟悉的呼吸,和背景深处极模糊、极遥远的集合号角。
“夏夏?”
李卫国的声音像一块被雨水冲刷过却依旧温厚的岩石,穿透两千多公里的湿冷。
喉头像被冰封。
千言万语哽在胸口,冻僵的嘴唇颤抖着,挤出几个浸透雨水的字:“卫国……我……我去找你。”
电话那端是令人窒息的死寂,电流不安的滋啦声和瓦片上如擂鼓的暴雨声交织。
一秒,或是一生那么漫长。
“好!”
斩钉截铁,毫无拖沓。
“等我消息,就这一两天。”
背景隐约传来快速有力的口令声。
通话断开。
我攥着冰凉湿滑的手机,站在樟树那点聊胜于无的遮蔽下,任暴雨冲刷。
卫国那个简短的“好”字,如同一小簇微弱的火苗,在胸腔最寒冷的角落猝然燃起,带着灼人的温度,烧蚀着周身的冰层。
县城边那间陈旧的小单间,开门就是一股混着霉味和木头潮气的浊浪。
一张铁床,一张掉漆的二手木桌,一把吱呀作响的塑料凳,墙角摞着个褪了色的塑料衣箱。
灰白的墙面上糊满了照片——军装笔挺的李卫国和裹在廉价红缎旗袍里的我,在那碗浮着零星牛肉片的清汤面“婚宴”上,笑容耀眼得没心没肺。
毛巾用力擦过湿透的头发,冰凉的布料贴上脸,狠狠揩去脸上横流的水渍。
湿透的衣服紧黏在皮肤上,寒气如细针,扎进骨头缝里。
离开!
这个念头如冰海下的暗流,汹涌地冲破了堤岸。
工作?
维系那个“家”的意义早已荡然无存。
目光落在墙上照片里李卫国肩章上多出来的那道杠。
他的担子从未减轻。
可最沉重的锚链——县城那套所谓“家”的象征,那把名为“血脉”却浸透算计的尖刀——必须斩断!
房子被他们寄生,成了颈上的枷锁!
一个落满厚尘的硬纸盒拖到摇晃的木桌上。
打开盒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雨夜王桂枝前文+后续
推荐指数:10分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雨夜王桂枝前文+后续》是作者 “会呻吟的杠精”的倾心著作,雨夜王桂枝是小说中的主角,内容概括:父母的新房是丈夫掏空积蓄买的,大哥却要求独占。“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父亲磕着烟袋闷声道,“你嫂子说得在理,是规矩。”母亲只会抹泪:“你哥孩子多负担重,你好歹读过书…多担待些……”雨夜被赶出家门,才发现房产公证书写着丈夫的名字。攥着150万房产证明逼哥嫂还钱,母亲却哭着拽我手臂:“你哥就这一个窝......
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