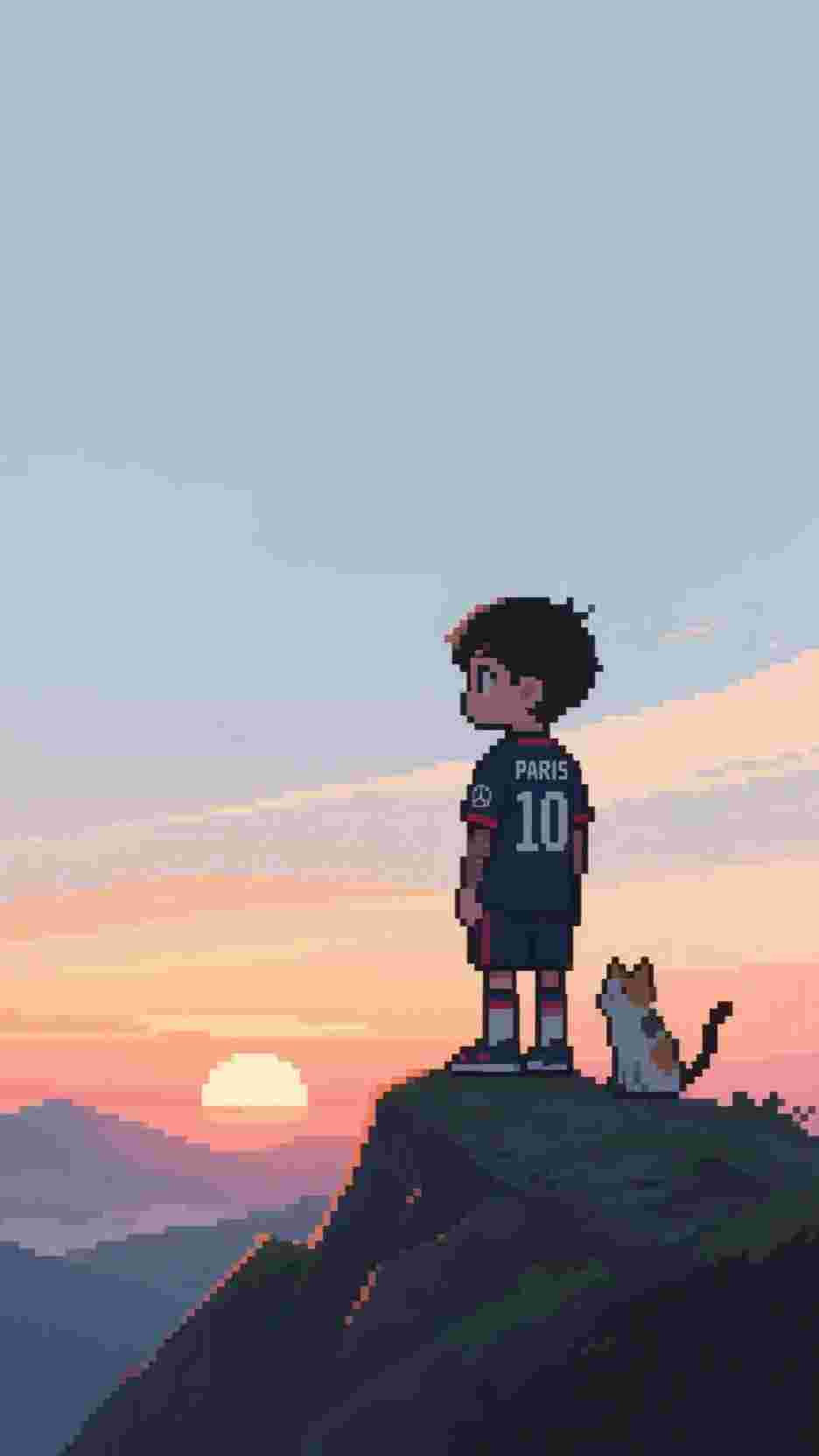了几个大学生,真诚地讲清楚了自己的困难。
那个时代的人都善良,四个大学生帮他把一包服装和一包丝袜认领了。
几个人终于挤进了车站。
没想到,上车时还是出了幺蛾子。
列车员就是不让吕晨和郑月上,非要他们办托运。
满眼的鄙夷,一脸的严肃,满嘴的规章制度。
吕晨最烦这种假大空。
两人只好跑到另一节车厢,那里的列车员是个男的。
眼看着开车的时间就要到了。
两人都心慌。
只见郑月快步迎了上去,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大哥,我和我哥都是待业青年”话还没说完,她一个趔趄,竟晕倒在列车员身上。
吓得那个男列车员手足无措。
混乱中吕晨连忙塞过去两包烟。
满脸堆笑:“同志,行行好!”
郑月趁机站直。
那列车员捏了捏烟盒厚度,小声笑骂:“真有你们的!”
眼睛却看向了远处。
两人如蒙大赦,麻溜地赶快上车。
一路艰辛,一路小心,就这样回到了南京。
房门吱呀推开时,霉味混着秦淮河的水汽扑面而来。
秦雨正踩着板凳,往剥落的墙皮上糊新领的营业执照,闻声回头,手里的浆糊碗“哐当”砸在地上。
“你……”她嗓子眼像被棉花堵住。
昏黄的十五瓦灯泡下,吕晨倚着门框,身体显得更瘦了。
那身出发前浆洗挺括的卡其布工装,如今裹满黑色的油渍和煤灰,肩头是一个被尼龙绳勒破的口子。
他脸颊凹陷,颧骨像刀削般突出来,青黑胡茬爬满下颌,嘴唇干裂翻着白皮。
最刺目的是那双眼睛——布满血丝的眼白里,瞳孔却烧着两簇炭火似的亮光。
灼得秦雨心口发疼。
这哪是那个在矿上绘图室里,连扳手都要按毫米间距摆放的技术员?
就是在劳改农场通宵守厕所,他偷懒打盹醒来时,眼皮耷拉着也还透着股活气儿。
可眼前的人,像刚从矿井里拖出来的煤球,浑身透着被碾碎又草草拼凑的灰败。
“怎么……弄成这样?”
秦雨声音发颤,扯过毛巾浸热水。
铝盆里倒映出他摇晃的身影,她才发现他左脚鞋帮裂了,露出的袜子洇着暗红。
吕晨却咧嘴一笑,露出沾着煤灰的牙:“成了!”
他反手拽进两个鼓囊的蛇皮袋,袋身被撑出尖锐棱角,拉链缝里漏出一截宝蓝色垫肩,“广州十三行

妻子秦雨吕晨秦雨无删减全文
推荐指数:10分
现代言情《妻子秦雨吕晨秦雨无删减全文》震撼来袭,此文是作者“平静的自由的心”的精编之作,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有吕晨秦雨,小说中具体讲述了:我就想拼命赚钱,这有什么错?再说了,我还不是想让我的老婆变成南京城里的富婆。可是,她倒好,不支持也就罢了。竟给了我记大耳光!1 躁动时代的气息是可以感受到的。一九八四年的风,就有股子鲜活的气息。现在,街面上的人都说,政策是真松了——个体户像雨后春笋般,噌噌往街面上冒;平反的老干部又挎着公文包重新进了......
第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