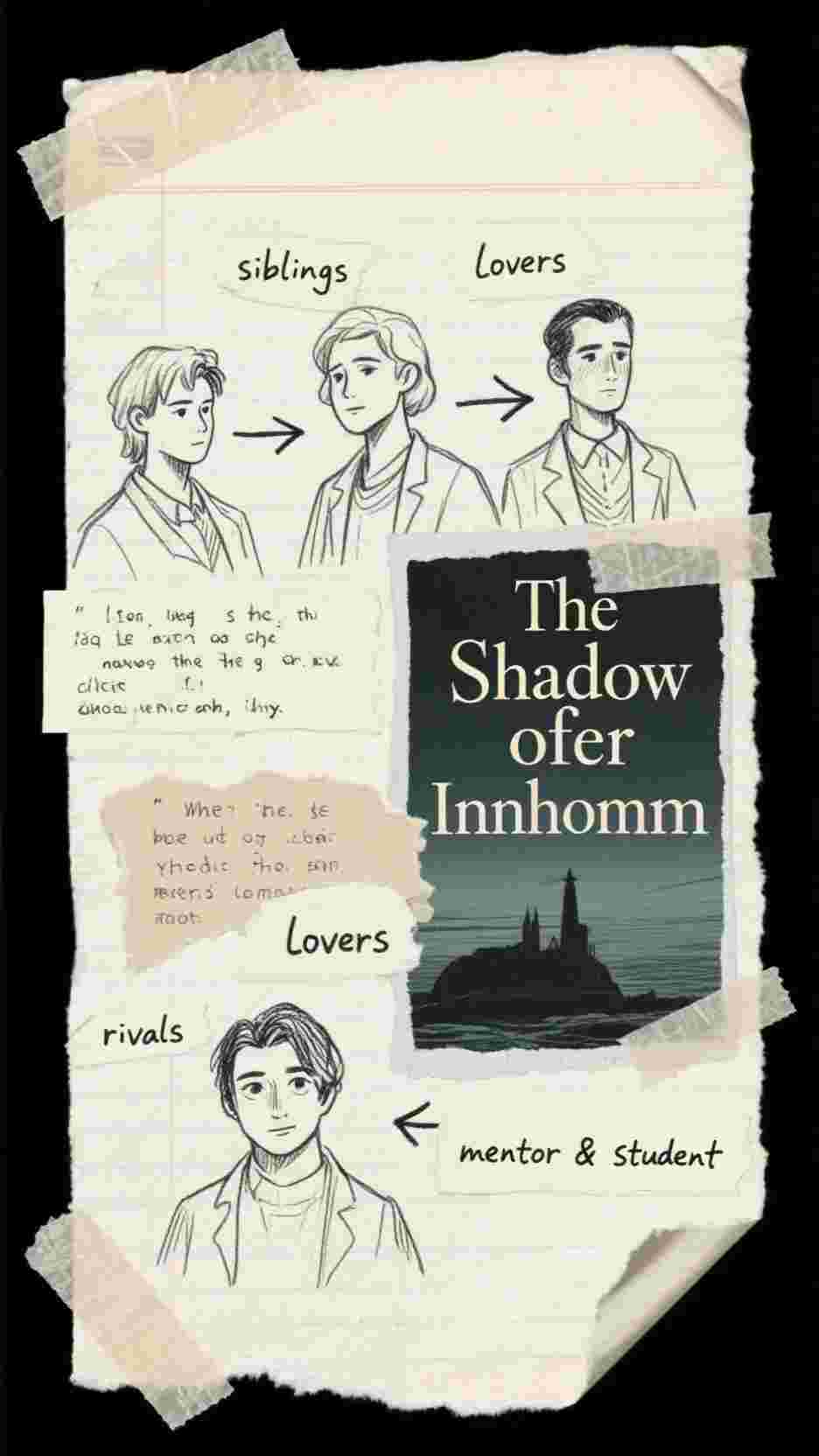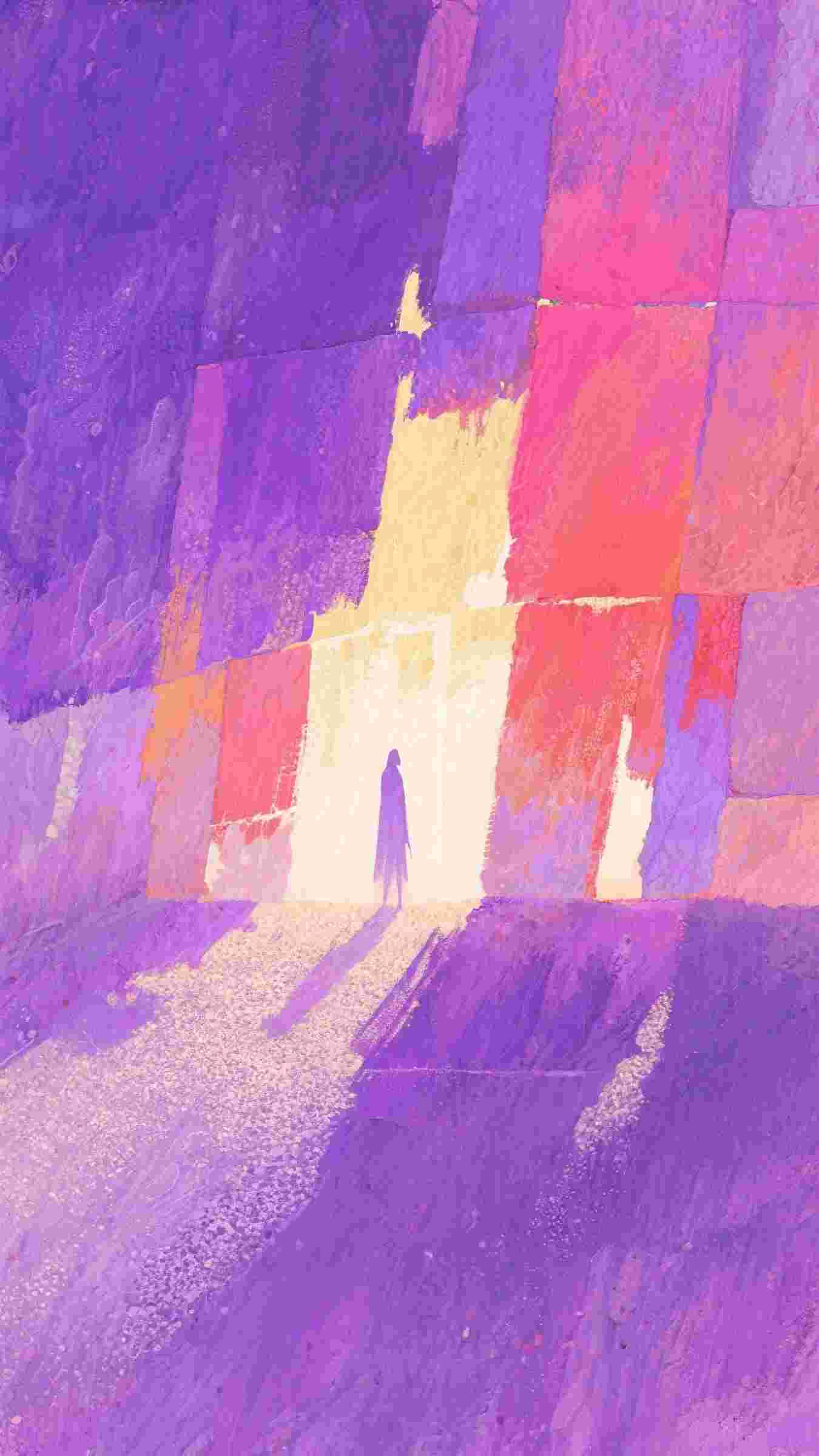泪水。
“看到朵朵…就不疼了。”
他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朵朵的头发。
朵朵小心翼翼地靠过去。
把小脸贴在他没受伤的脸颊边。
“爸爸要快点好起来…”陈锋的眼圈瞬间红了。
他闭上眼。
喉结剧烈地滚动着。
“嗯…爸爸答应你…”晚上。
朵朵被苏晴带走了。
病房里又只剩下我们。
护工打来了热水。
我拧了毛巾。
给他擦脸。
擦手。
他像个木偶一样任我摆布。
只是眼睛一直追随着我。
“月月…”在我收拾东西准备去倒水时,他忽然开口。
我停下。
“医药费…我会转给你…”他声音很轻。
“不用。
你先养好伤。”
我说。
他沉默了一下。
“下周一…”他艰难地吐出那个日期,“我…去不了…我知道。”
我端起水盆,“手续的事,等你出院再说。”
他看着我。
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
又迅速黯淡下去。
“你…还会来吗?”
他问,声音带着不确定的卑微。
我没回答。
端着水盆走了出去。
后面几天。
我白天上班。
下班去医院。
给他送点清淡的粥和汤。
他恢复得不算快。
脑震荡的后遗症让他经常头晕。
恶心。
但情绪还算稳定。
只是每次看到我。
眼神里都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探究。
和极力压抑的期待。
他不再提离婚的事。
我也不提。
我们默契地维持着一种虚假的平静。
像踩在薄冰上。
一周后。
他出院了。
头上的纱布拆了。
留下一道暗红色的疤。
在额角。
像一条丑陋的虫子。
他坚持要回我们那个家。
“还有些东西…要收拾。”
他这样解释。
我没反对。
打开门。
家里还维持着他出事前的样子。
冰冷。
空荡。
茶几上。
那份皱巴巴的离婚协议书。
还静静地躺在那里。
像一个无声的讽刺。
他走过去。
拿起那份协议。
看了一会儿。
然后。
慢慢地。
一点一点地。
把它撕成了碎片。
雪白的纸屑。
纷纷扬扬地洒落。
像一场迟来的祭奠。
他转过身。
看着我。
眼神是前所未有的清醒。
和一种近乎孤注一掷的平静。
“邹月。”
他叫我的全名。
“我们谈谈。”
我看着他额角那道疤。
点了点头。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
隔着一段距离。
像谈判的双方。
“那天晚上…”他开口,声音低沉,“我是真的…想死。”
我放在膝盖上的手,微

离婚前夜,前夫他后悔了番外
推荐指数:10分
无广告版本的现代言情《离婚前夜,前夫他后悔了番外》,综合评价五颗星,主人公有陈锋月月,是作者“卡里多斯”独家出品的,小说简介:我拎着菜进门。钥匙刚插进锁孔。门从里面被拉开了。陈锋站在门口。他脸上有没藏住的慌张。“今天这么早?”他声音有点干。“嗯,菜场人少。”我低头换鞋,手里装着排骨的塑料袋窸窣响。他堵在玄关。没像往常那样伸手接我手里的东西。“站这儿干嘛?”我抬头看他。他眼神躲闪了一下。“没…没什么。”他侧身让开,“刚在…找......
第1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