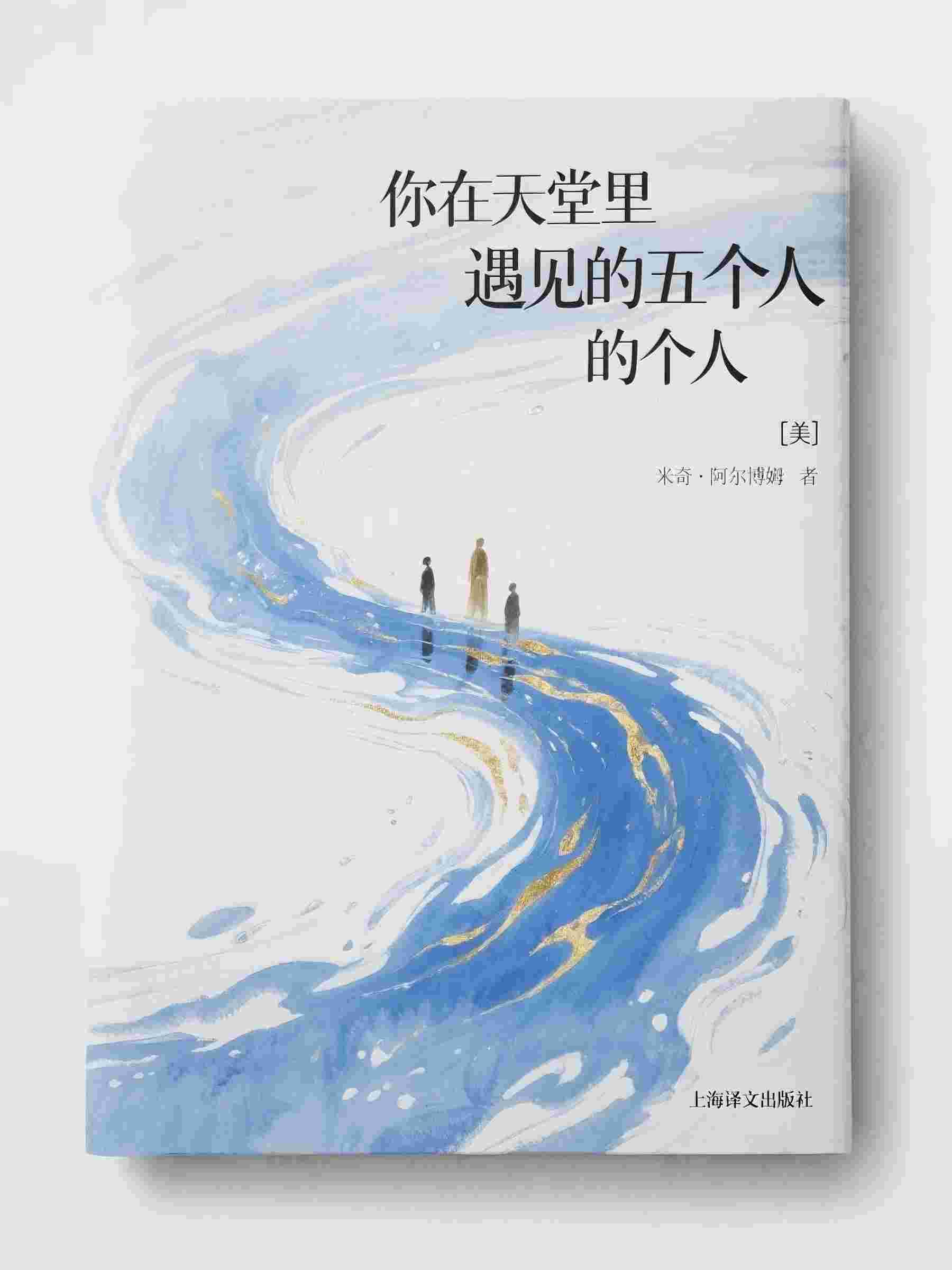就不知道烂哪儿去了,只剩下个黑洞洞的窟窿。
窟窿顶上,几根朽得发黑的房梁斜斜地戳出来,雨水顺着梁头往下滴。
可就在那梁头底下,有人用湿泥巴糊上去几片枯黄的大芭蕉叶,叶子被雨水打得半卷着,边缘耷拉下来,活脱脱像个张着大嘴、准备吞掉光线的怪兽脑袋!
弹幕疯了似的往上蹦。
“卧槽!
后现代废墟美学!
绝了!”
“坐标!
求大佬给个坐标!
这地方太有感觉了!”
“像不像被遗忘的远古祭坛?
神秘感拉满!”
“楼上懂个屁,这叫原生大地艺术!
浑然天成!
高手在民间啊!”
“明天就去打卡!
有没有组团的?”
视频下面,定位清清楚楚:柳溪村,赵家老宅。
手机屏幕的光映着我脸上,那点光又冷又硬。
我低头看看手里啃了一半、硬邦邦的冷馒头,再看看屏幕上那被吹成了“顶级艺术”的、我自己住了二十多年的破狗窝。
一股邪火猛地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烧得我五脏六腑都跟着疼。
手一哆嗦,那半个冷馒头“啪嗒”一下掉进脚边接雨水的搪瓷盆里,溅起几滴浑浊的水花。
去他妈的顶级艺术!
去他妈的浑然天成!
这破院,这烂瓦,这漏风的墙,就是穷!
就是惨!
就是被人坑得血本无归!
三天前……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知了在村口那几棵歪脖子老槐树上扯着嗓子嚎,吵得人心烦意乱。
我穿着那件洗得发白、印着“XX物流”的旧工装T恤,脖子上搭条看不出本色的毛巾,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淌,在后背洇开一大片深色。
手里拎着扫把,正跟堂屋里积了八百年的陈年老灰较劲。
灰尘扬起来,呛得我直咳嗽。
就在这灰头土脸、咳得撕心裂肺的当口,院门口传来“嘎吱”一声刺耳的刹车响。
声音不大,但在这寂静得只剩下知了叫的晌午,显得格外扎耳。
我捂着嘴,眯缝着被灰迷了的眼睛朝外看。
一辆锃亮得能照出人影的白色宝马,稳稳当当地停在了我家那歪歪扭扭、勉强能算个门的破木栅栏外面。
跟周围这破败景象一对比,那车简直像个天外来物,晃眼。
车门开了,先伸出来的是一只脚。
脚上踩着一双尖得能戳死人的黑色细高跟鞋。
那鞋跟,少说也得有十厘米。
然后,是一

被骗30万后网红美女哭着求我合作抖音热门后续+全文
推荐指数:10分
小说《被骗30万后网红美女哭着求我合作抖音热门后续+全文》是作者“东莱文砚”的精选作品之一,剧情围绕主人公抖音热门的经历展开,完结内容主要讲述的是:>我带着城里打工攒的30万回村,准备开农家乐振兴家乡。>高薪请来的美女设计师林菲菲量尺寸时,旗袍开衩里的大长腿晃得我眼晕。>她指尖划过我手臂:“赵老板心跳好快,是热还是紧张?”>结果她卷款跑路,留给我一张狗爬似的设计图。>我蹲在漏雨的破屋里啃冷馒头,却刷到同城热搜:#废弃农院惊现顶级艺术#。>点开一......
第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