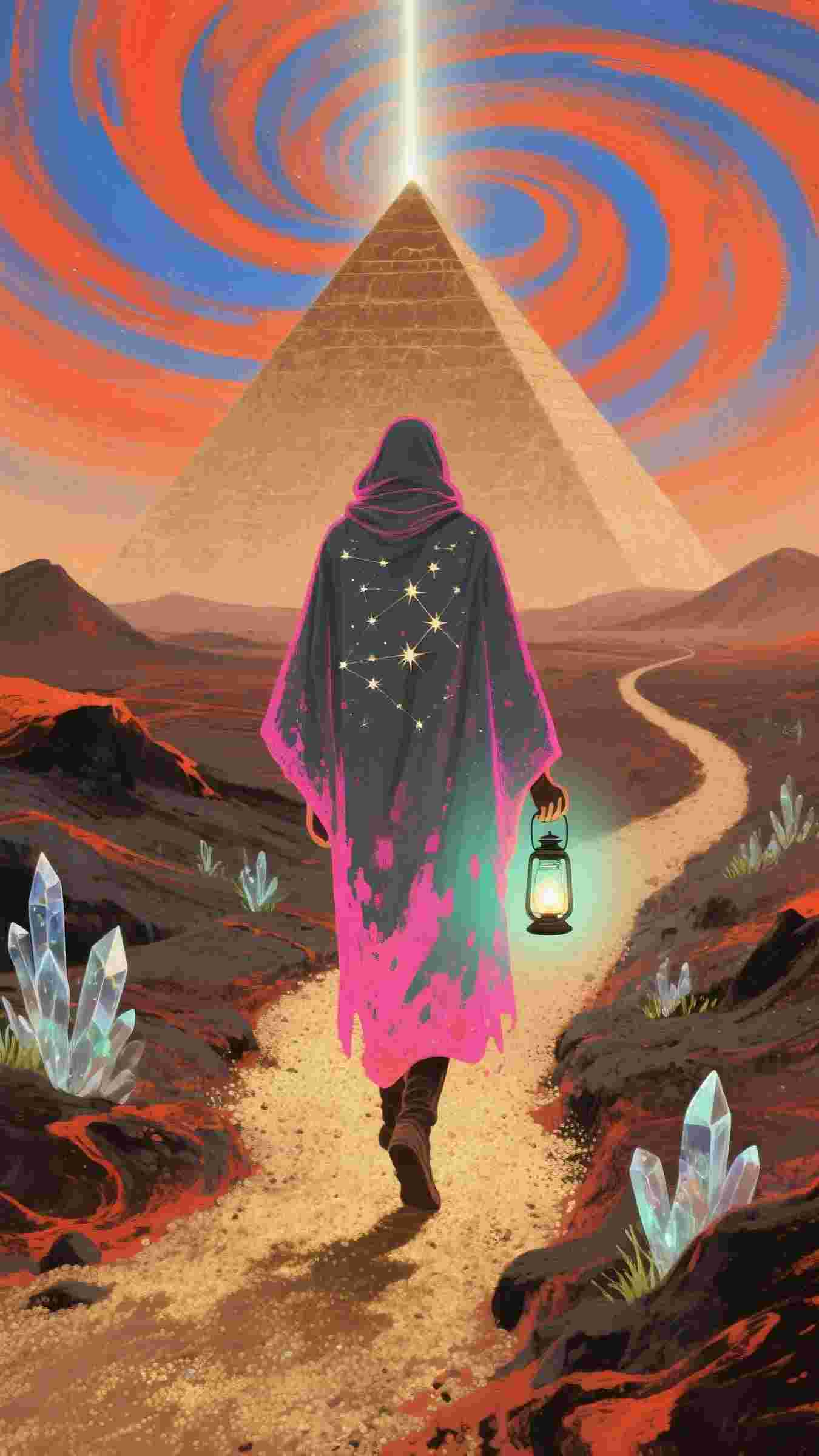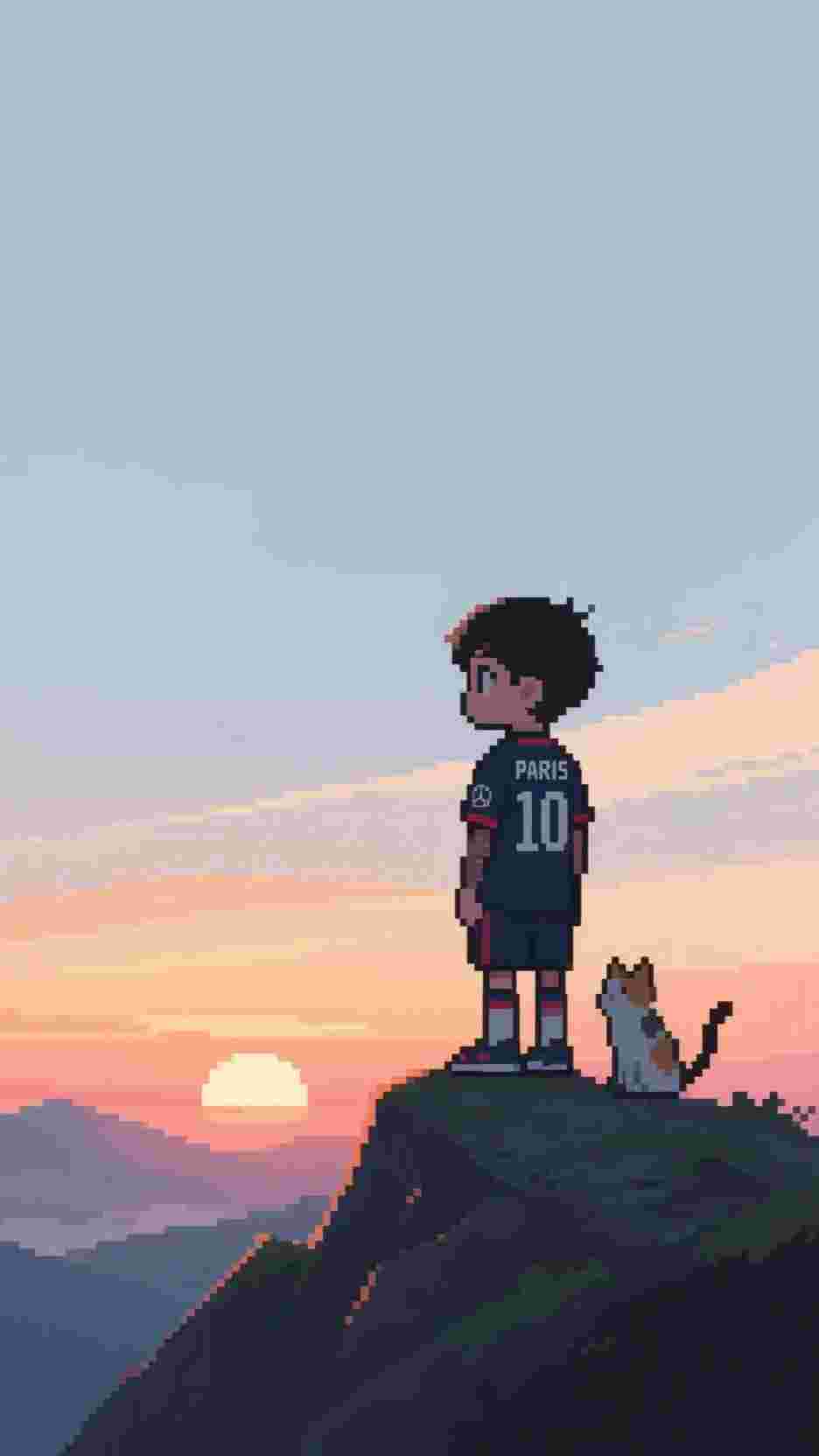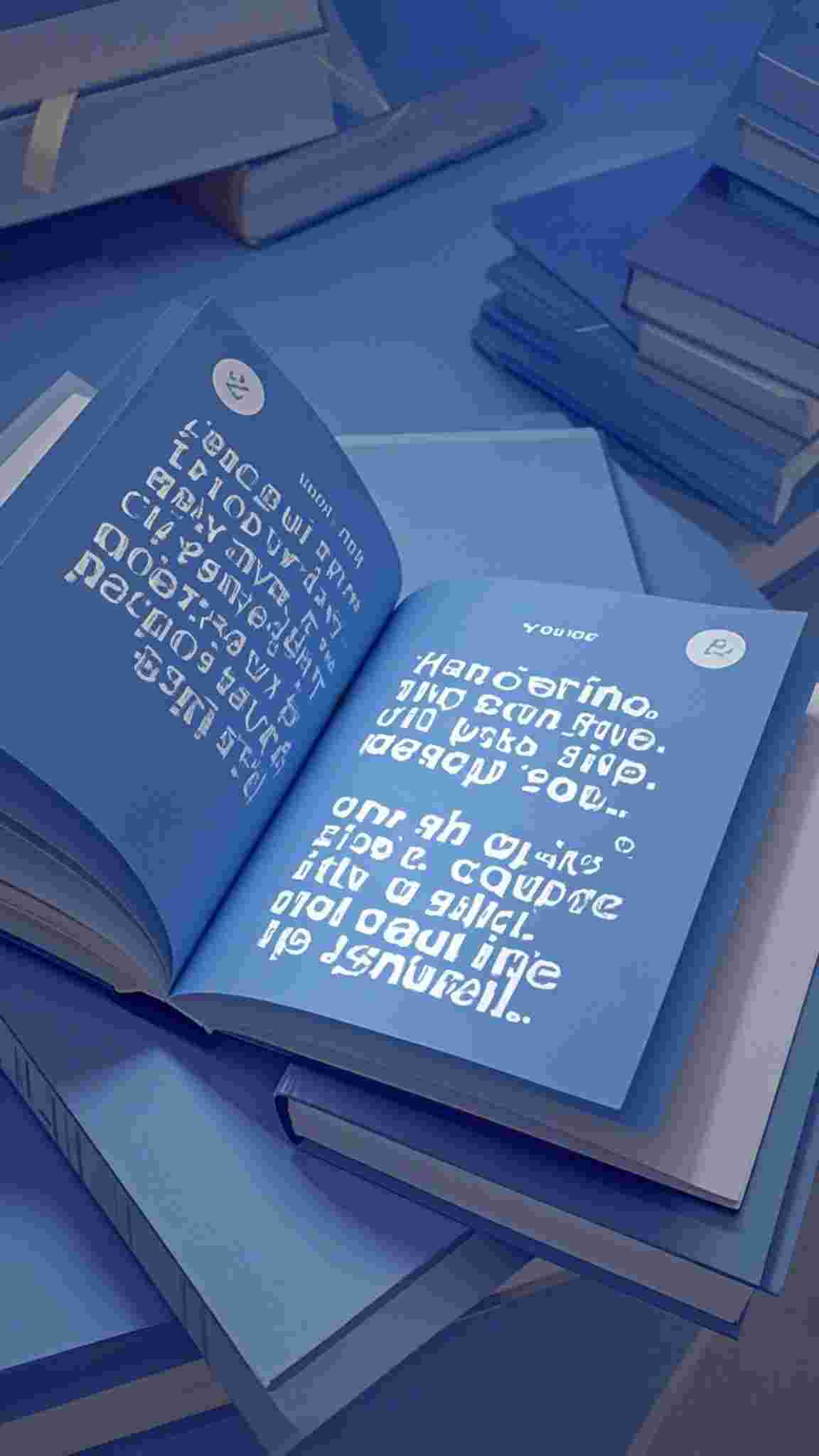在她面前,“总利润十七贯三百六十二文,损耗是被阿竹偷吃的两斤虾仁。”
人群里有人笑出声。
阿竹红着眼眶抹脸:“我就偷吃了两回!”
周氏的脸涨成猪肝色,转身要挤出去,被赵知府叫住:“周娘子,百匠坊要的是能让百姓吃得上、吃得好的手艺。”
他指了指我柜上的罐子,“你家米铺要是能把米煮出这鲜味,我亲自给你题匾。”
哄笑声里,我余光瞥见街角跑过来个小厮。
他挤到我身边,压低声音:“沈娘子,陆家绸缎庄被官府封了。
说是漕粮案里贪了粮银,陆大夫人今早咳血晕了,陆公子……”他顿了顿,“没找着人。”
我攥着账本的手紧了紧,抬头看见“知味坊”的匾在风里晃。
十年前我蹲在陆家灶房烧火,陆明川说等他中举就娶我;三年前他骑高头大马跨进尚书府,我蹲在老槐树下烧他的旧衫;今儿他失踪了,我站在自己的铺子里,听着铜钱响得像首曲子。
夜里打烊,阿竹收拾完最后一只碗:“夏夏,我明儿想把老家的表妹接来,帮着包馄饨皮。”
她戳了戳我怀里的陶瓮,“你攒的碎银,该换成新瓦罐了。”
我没应她。
后院的槐叶沙沙响,像极了十年前老槐树下烧布衫的噼啪声。
我望着天,轻声说:“我不欠你们了。”
第二日开门,日头照样晒得匾发亮。
阿竹系着新围裙喊:“头锅汤开了!”
我舀着高汤,看顾客排到了巷口——这一回,没人能让我关铺子,没人能让我等谁回家。
第三日晌午,我在后院捣鼓新汤料。
瓦罐里的菌子刚泡开,突然听见院门外“咚”的一声。
“沈娘子——”是个生人的声音,带着股子狠劲。
我握着捣杵的手停了停,菌香混着风飘过来。
该来的,总要来的。
6 雨夜还债情难了债要还,情该了我正蹲在瓦罐前捣菌子,阿竹的脚步声从院外急冲冲撞进来。
“夏夏!”
她喘气声比灶火还急,“门外来了三个戴白麻的,说是陆家旧仆,堵着门槛骂你偷东西!”
我手底下的捣杵顿住。
菌香混着潮湿的土味漫上来——五年前我在陆家库房偷边角料的事,到底被翻出来了。
那时我接了绣娘的私活,给小公子做虎头鞋,布料不够,鬼迷心窍顺了半匹月白杭绸。
“

十年童养媳,焚衣断过往明川沈知夏无删减+无广告
推荐指数:10分
以明川沈知夏为主角的现代言情《十年童养媳,焚衣断过往明川沈知夏无删减+无广告》,是由网文大神“老阿佳”所著的,文章内容一波三折,十分虐心,小说无错版梗概:1 火烧旧衣断前缘我给陆家做了十年童养媳,他成亲那天我烧了他的旧衣火烧槐树前,我数完了最后一块碎银我往灶里添了把柴火,木柴噼啪响着,小米粥在砂锅里咕嘟冒泡。干桂花是上个月捡的,晒得金黄,我捏着两片扔进锅里,甜香混着米香飘出来——明川最爱这口。他说过,等中举那日,要穿新裁的青衫,亲自去祠堂给我敬茶。我......
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