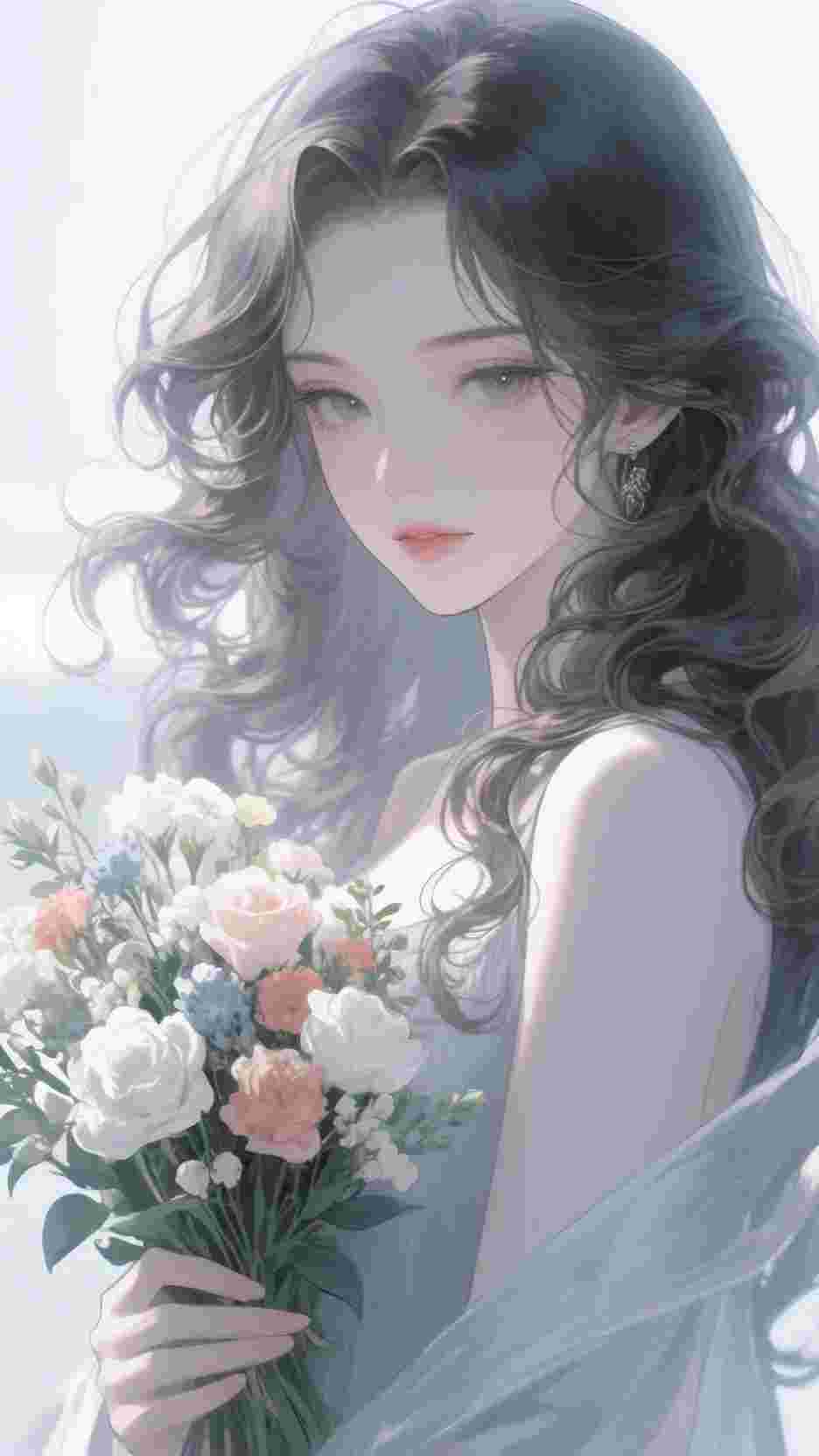木非铁,光滑如墨玉。
轿帘低垂,同样是厚重的纯黑,密不透风。
抬着轿子的,是四个身形异常高大、笼罩在同样纯黑色、宽大得如同裹尸布般斗篷里的人影。
他们的脸完全隐藏在斗篷的深重阴影之下,看不到任何五官,甚至连身体的轮廓都模糊不清,仿佛本身就是雾气凝结而成。
动作僵硬、刻板,如同提线木偶,步伐却奇异地完全一致,踏在松软的泥地上,没有发出丝毫声响。
整个坟地陷入一片死寂。
手臂淌血的哑伯、枪口冒青烟的张乾、倒地的村民…所有人的动作都凝固了,目光如同被无形的磁石吸引,死死钉在那顶突兀出现的黑色轿子上。
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无法抗拒的、压倒一切的恐惧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每一个人,连思维都被冻结。
黑轿径直滑行到深坑边缘,正对着坑底泥泞中的我。
四个抬轿的黑色人影同时停下脚步。
其中一个,动作僵硬地、如同折断的枯枝般弯下腰。
一只同样被纯黑布料包裹、看不出形状的手,从宽大的袖袍中伸了出来。
那只手,精准地、毫无停顿地抓向了坑底的我。
没有选择,没有挣扎,甚至没有反应的时间。
那只黑手如同铁钳,轻易地抓住了我破烂寿衣的后领,将我整个人如同拎起一件没有生命的货物般,毫不费力地提了起来。
我浑身是伤,意识在崩溃边缘,连一声惊呼都发不出,只能徒劳地感受到那只手上传来的、不属于活物的、绝对的冰冷和力量。
黑手随意地一甩。
我的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轻飘飘地飞起,撞向那顶纯黑的轿子。
厚重的黑色轿帘在接触到我身体的瞬间,如同水面般微微波动了一下,悄无声息地向内分开一道缝隙。
缝隙后面,是更加深邃、更加纯粹、仿佛连宇宙都能吞噬的黑暗。
就在我的身体即将被那黑暗彻底吞没的最后一刹那,我下意识地、绝望地朝那缝隙深处望了一眼。
没有想象中的怪物。
没有蠕动扭曲的黑暗。
只有一张脸。
一张极其熟悉、却又陌生到令人骨髓冻结的脸。
那是……轿帘如同垂死的天鹅之翼,在我视线聚焦、大脑即将辨认出那张脸的瞬间,轻柔地、无声地垂落下来。
隔绝了视线,隔绝了光,也隔
棺中祭祀番外 第11章 试读
爱吃豆浆煮鲤鱼的乔元 著 抖音热门现代言情 来源:cddp 时间:2025-08-17 22:37:18

棺中祭祀番外
推荐指数:10分
现代言情《棺中祭祀番外》目前已经全面完结,抖音热门之间的故事十分好看,作者“爱吃豆浆煮鲤鱼的乔元”创作的主要内容有:那天,我假扮记者,溜进了雾隐村,为的是村里传得神乎其神的长生秘宝。结果呢?当晚就犯了忌讳。一帮村民二话不说,给我套上死人穿的寿衣,硬生生塞进了一口薄皮棺材里。我喘不上气,紧贴着我的那具冰冷“尸体”却突然动了,一个声音贴着我的耳朵响起,嘶哑又瘆人:“别怕…我也是…活人…”1 雾隐诡井雾隐村这鬼地方,雾......
第1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