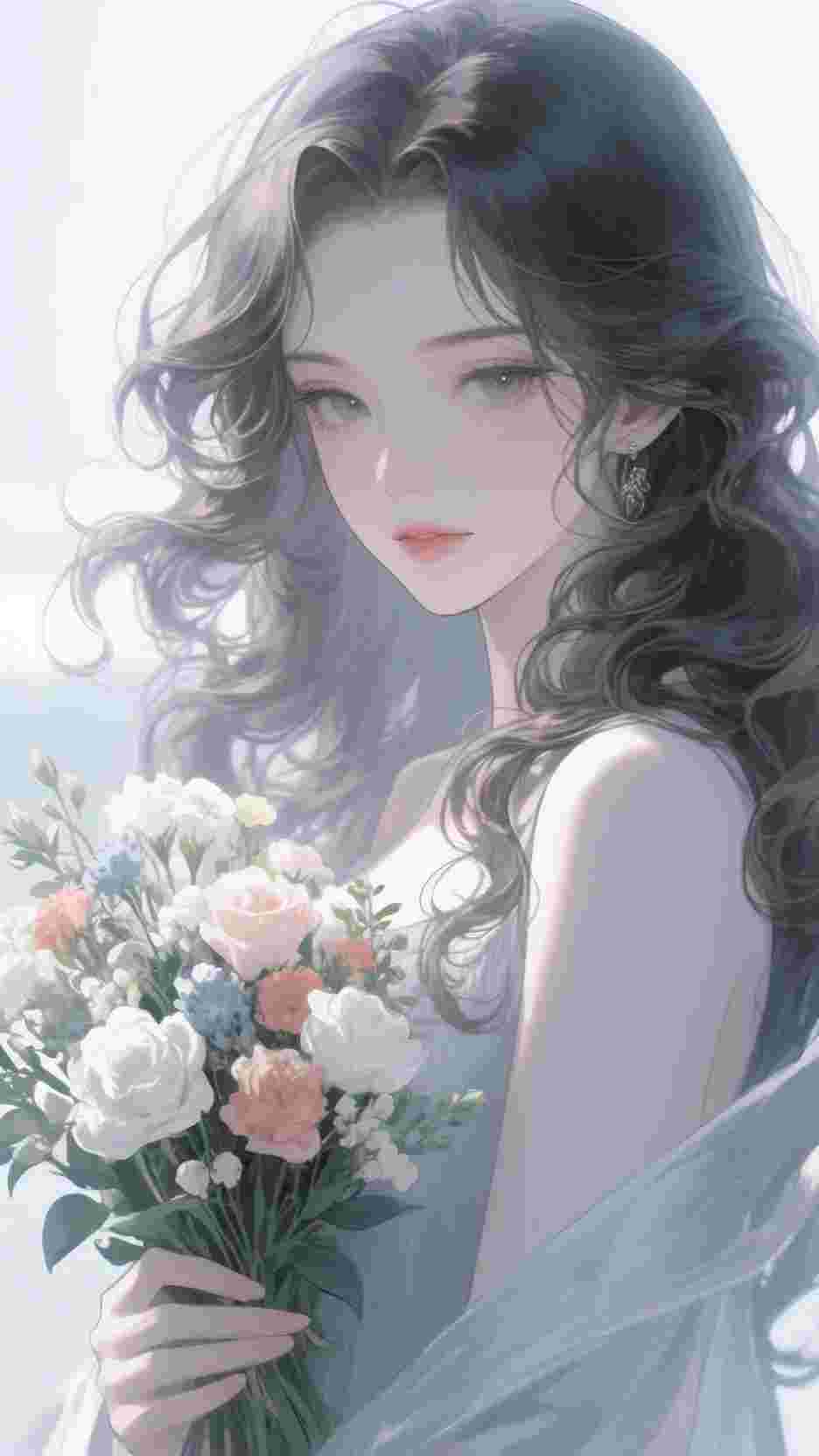丝极快的、或许是怜悯、或许是更复杂难言的微光,但瞬间被冰寒取代,“它将如附骨之蛆,日夜啃噬你残破的五脏六腑,那是万毒噬心,冰火熬魂的痛苦。
活着,从此便要倚赖此毒物续命,至死方休,永不超脱。”
巨大的绝望混合着药鼎散发的辛腥气味狠狠攫住了柳疏疏。
“沈砚……”这个名字像淬毒的冰棱,从她齿缝里挤出,带着淋漓的血腥气。
耶律崇(她此刻虽不知其名,但这个男人无形中有了代号)注视着她灰死眼底骤然迸出的、如同地狱业火般不屈的幽芒,缓慢而清晰地说出五个字: “活下来。”
那声音冷硬如北地冻岩,每个字却拥有着凿穿冰层的万钧力量:“活到有力量能亲自回到那座囚禁你的城池,能亲眼看着那个剜你血肉、断你亲缘的男人——跪在你脚下的那一天。”
如同荒原上最倔强的荆棘种子,被这冰冷残酷却蕴含一丝生机的宣言狠狠砸进了冻土最深处。
活下去。
为了复仇的火焰。
火焰虽冷,足以焚尽过往。
耶律崇的眼神或许冰冷依旧,但柳疏疏破碎眼底那点燃起的冰冷火焰,开始有了具体的形状。
4 鬼手药师十年光阴如漠北的风沙,粗糙而迅疾地掠过荒原。
曾经在绝望中瑟瑟发抖的柔弱药人柳疏疏,早已被呼啸的风雪、永无止境的万毒噬心之痛、以及淬骨焚心的恨意重新熔铸。
续命膏的药力如同跗骨之蛆,日夜纠缠着她的残躯,每一次发作都像万载寒冰与地狱熔岩在她体内反复交煎。
她的生命像悬在千仞冰崖边的一粒沙,被那诡异的毒膏勉强粘附着。
但正是这无尽的折磨,让她的灵魂如同北荒荒漠里最坚韧的刺棘草,在绝死之境深深地扎下根,于毒火灼烧中伸展出淬毒的锋芒。
她成了这片广袤草原上最神秘莫测的存在——“鬼手药师”。
厚重的、足以遮蔽风雪与窥探目光的毡帽几乎永不摘下,掩盖了那曾被沈砚视若敝履、如今却已染尽风霜的容颜。
露出的唯有一双淬毒的眼眸——冰冷、幽深、波澜不起,如万古寒潭。
人们讳莫如深,只知鹰王帐下有这样一个女子,接得了连萨满也束手无策的奇毒恶疮,要的价码也足够震慑所有心怀不轨之徒。
她的

寒髓煞沈砚苏挽月全局
推荐指数:10分
很多网友对小说《寒髓煞沈砚苏挽月全局》非常感兴趣,作者“海若昕印”侧重讲述了主人公沈砚苏挽月身边发生的故事,概述为:1 心头血祭南黎永昭十年的隆冬,空气里凝着能将骨缝都冻裂的寒意。沈将军府西角院偏僻的厢房里,炭火奄奄一息,豆大的烛光在壁上投下柳疏疏枯槁孤寂的影子。窗外北风呼啸,撕扯着枯枝败叶,呜咽声如同弃婴彻夜不休的啼哭,一声声钻进她的耳朵,刮着她的脑仁。她像个没有重量的影子,悄无声息地跪在拔步床厚重的紫绒帐幔阴......
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