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
我打开微信,朋友圈列表只剩下几条广告。
几百个联系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空壳。
我不敢再点开通讯录。
那种“你以为你还活着,但所有人都不记得你”的感觉,比死亡更彻底。
信不仅能改写我的文字,还能改写我在他人记忆中的“位置”,直到我被完全替换。
我开始做笔记,用纸和笔,把我知道的一切写下来。
但每当我回头重读,总会发现字句被篡改。
比如我写:“我在梨溪路看见她消失。”
第二天看,这句话就变成了:“我站在梨溪路,等待消失。”
我连自己的回忆都开始不信了。
我把所有的纸条塞进行李箱,打算远离这座城市,哪怕几天也好。
可我刚打上出租车,导航却一直绕回同一条高架。
司机说:“你刚才上来的时候,说你是来找信的。”
我顿时后背发凉:“我没说过这句话。”
他不再说话,表情开始空洞,嘴角却上扬了几度,像一张被强行扯开的笑脸。
我让他停车,他没有回应。
我大喊,他还是不开门。
直到我在后座车窗上,看见一张脸贴在外面玻璃上——是那个女孩。
她的脸极近地贴着车窗,眼神空洞,嘴里轻轻张合。
我看见她对着我说:“我在信里,看你很久了。”
玻璃上泛起雾气,又浮现出那行字:“你,是我吗?”
这是我第一次在完全无控制的情况下,与信的“核心意识”正面对视。
下一秒,我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车不见了,人不见了。
我一个人躺在梨溪路地铁站口的台阶上。
像是从信中被“退回”了现实。
但我知道,那已经不再是我的现实。
我回到家,发现门口信箱被人打开,里面静静躺着一封信。
没有邮戳、没有地址。
信封熟悉得像梦里拿过千万次。
我不再犹豫,打开它。
里面不是记录,不是日记,而是几页我从未写过的文字。
开头是:“你好,沈礼。
你已经替我写了大部分内容了。
只剩最后几段,就可以交给下一个人。”
“感谢你存在过。”
我眼泪莫名地流下来。
不是悲伤,是一种存在即将被归档的感受。
信纸最底部,是一张打印纸的复印影像:一个人坐在桌前,正低头写着什么。
我认出那是我。
但桌上的信封上,写的名字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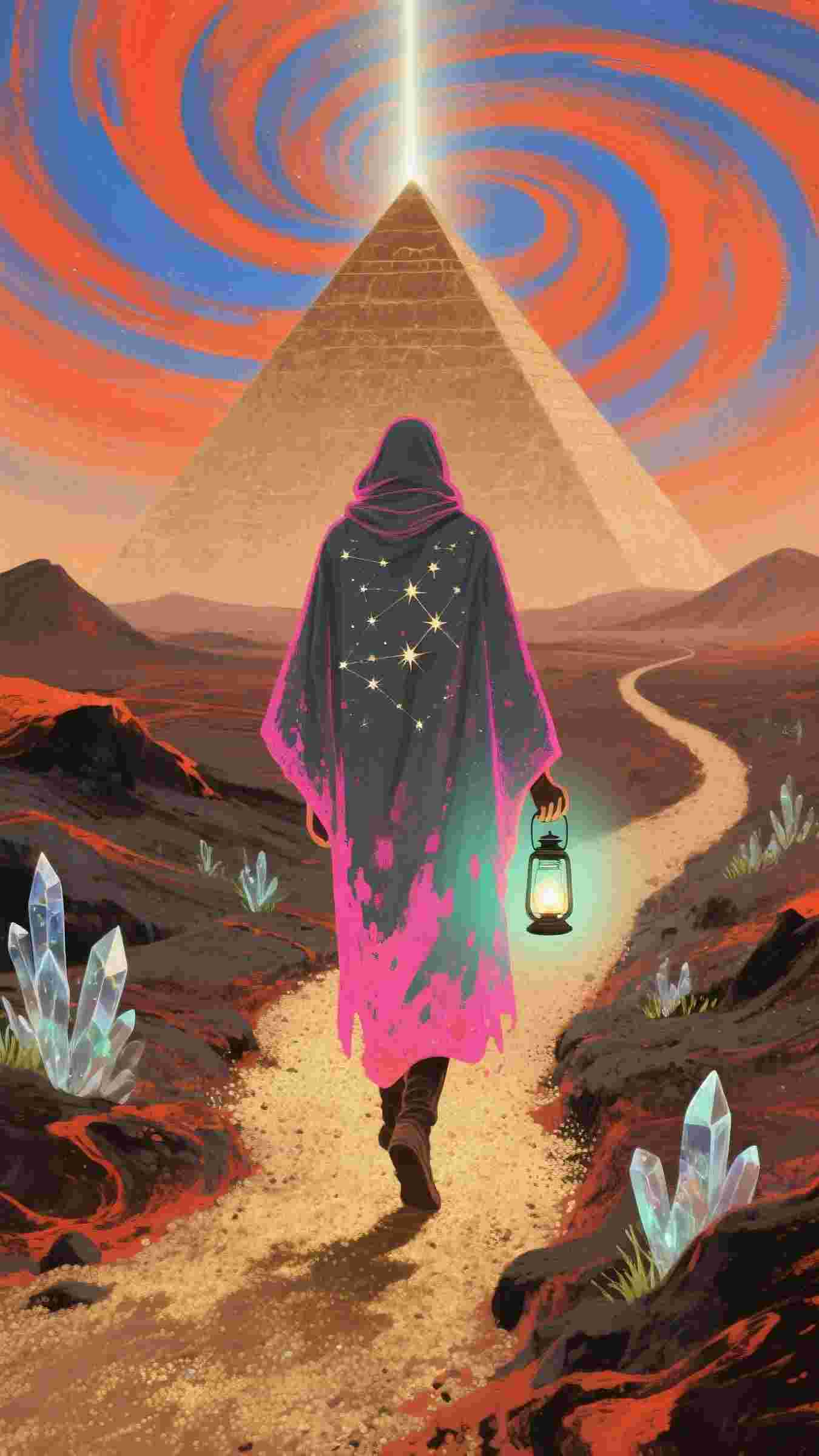
失物招领处的那封信无删减全文
推荐指数:10分
以现代言情为叙事背景的小说《失物招领处的那封信无删减全文》是很多网友在关注的一部言情佳作,“照影千川”大大创作,抖音热门两位主人公之间的故事让人看后流连忘返,梗概:第一章|那封信的照片「如果你在地铁站,看见那扇白色的门,请不要推开。」 这句话最早是我在知乎某个冷门帖子底下看到的。配图是一张模糊的照片,背景是某地铁站一角,角落贴着一个歪斜的红字纸牌:「失物招领」。而图片的焦点,是一个泛黄的信封,静静地躺在玻璃台面上。 信封上用红墨水写着:「只给失主」。刚看到那张......
第14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