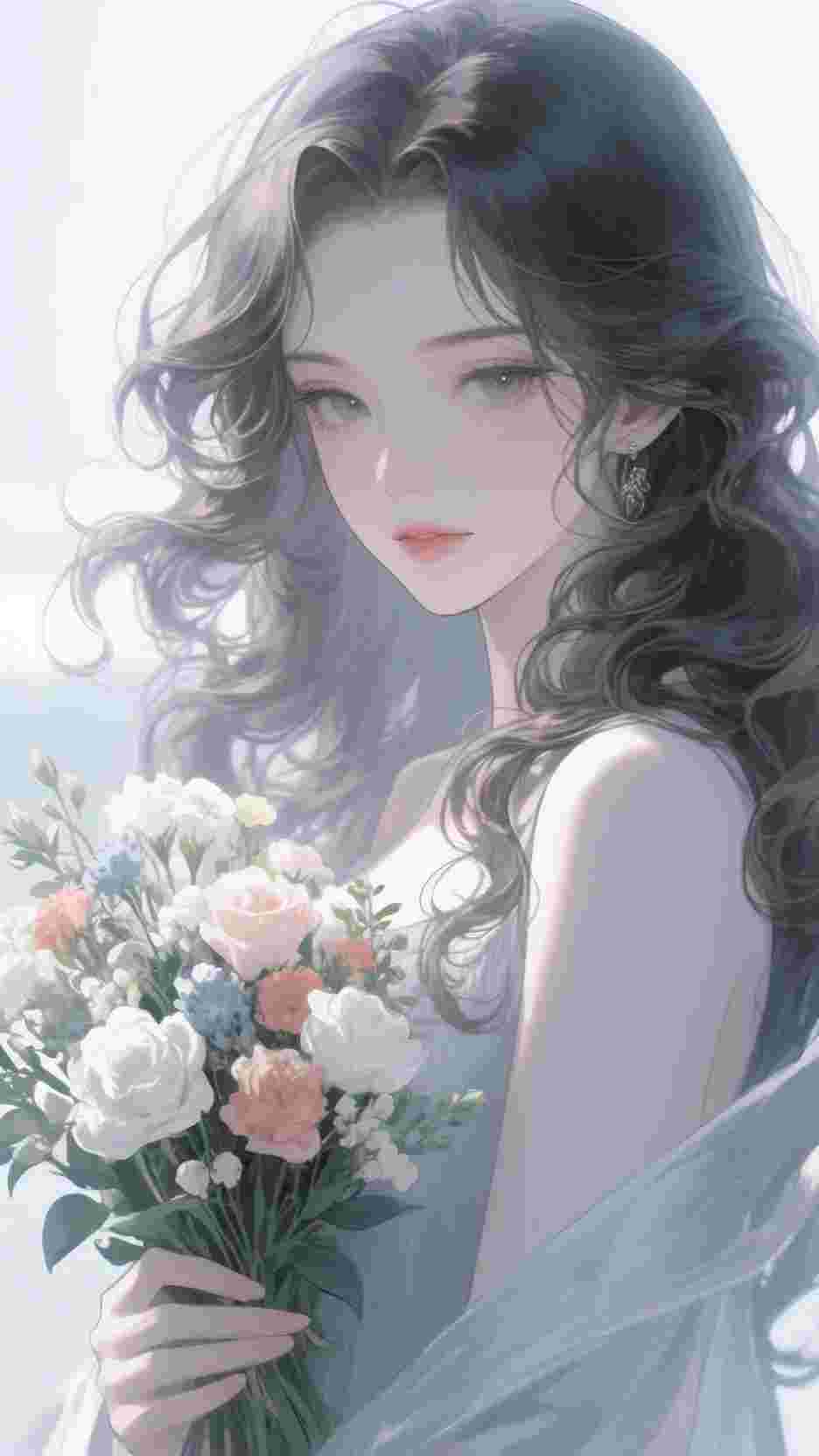的呓语。
原来,真相不是利剑。
它是一把锈钝的、沾满污垢的旧锯子,在早已腐烂的心口,不紧不慢地来回拉扯。
没有瞬间的剧痛,只有绵长无尽的、令人窒息的钝痛,一下下,锯开血肉,锯断筋骨,锯碎这三年来所有自欺欺人的幻梦。
我像个提线木偶,用尽全身力气,才把僵硬的手臂抬起来,用力地、坚定地推开他沉重的身体。
顾淮予毫无防备,闷哼一声,向后趔趄,脊背重重撞在冰冷的墙壁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他吃痛地皱紧眉头,眼神涣散,茫然地看着我,似乎不明白眼前这个“薇薇”为何突然变得如此粗暴。
我甚至没有再看那张让我痴迷了三年的脸。
身体里有个地方彻底碎了,碎得无声无息,却再无修复的可能。
我沉默地转身,脚步有些虚浮,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童,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决绝,一步一步走回那张烛光摇曳的餐桌旁。
桌上的冷盘,精心摆盘的牛排,甚至那瓶暗红色的酒,此刻都蒙上了一层令人作呕的油腻。
烛火跳动着,将一切映照得扭曲而诡异。
我拉开椅子,坐下。
动作僵硬得像生锈的机械。
银质餐刀冰冷的触感透过指尖传来。
我拿起它,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泛白。
刀尖对准盘子里那块早已冷透、纹理僵硬的牛排,狠狠地切了下去。
刀刃划过冷硬的肉块,发出极其刺耳、令人牙酸的摩擦声——“滋啦!”
那声音尖锐地穿透死寂的空气,像是指甲刮过玻璃,又像是某种不堪重负的东西终于彻底断裂。
这声音似乎也惊动了靠在墙边的顾淮予。
他混沌的脑袋艰难地转动了一下,涣散的目光终于聚焦了一丝,带着被惊扰的烦躁和不耐,含糊地嘟囔了一句:“吵什么……”我握着刀的手,停顿在半空中。
刀尖悬在冷硬的牛排上方。
刺耳的摩擦声消失了,餐厅里只剩下他粗重的呼吸和我自己擂鼓般的心跳。
我缓缓抬起头,目光越过摇曳的烛光,落在他身上。
那张英俊得足以令无数人沉沦的脸,此刻在酒精和混乱的欲望下显得如此陌生,甚至……丑陋。
那双曾让我沉溺其中的深邃眼眸,此刻只剩下迷茫和因被打扰而升起的薄怒。
原来剥开那层华丽冰冷的“顾太太”外壳,

金牌替身:顾总,白月光过期了番外
推荐指数:10分
小说《金牌替身:顾总,白月光过期了番外》,此书充满了励志精神,主要人物分别是白月光顾淮予,也是实力派作者“东方嵐”执笔书写的。简介如下:>结婚三周年纪念日,我亲手布置烛光晚餐。>丈夫醉醺醺回家,却把我错认成他的白月光:“薇薇,别离开我。”>第二天我摘下婚戒,留下字条:“替身合约到期,祝你们百年好合。”>消失三个月后,国际设计大赛颁奖现场。>聚光灯下,主持人宣布:“本届金奖得主——Eva Su!”>我挽着顾淮予死对头的手臂优雅登台。>......
第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