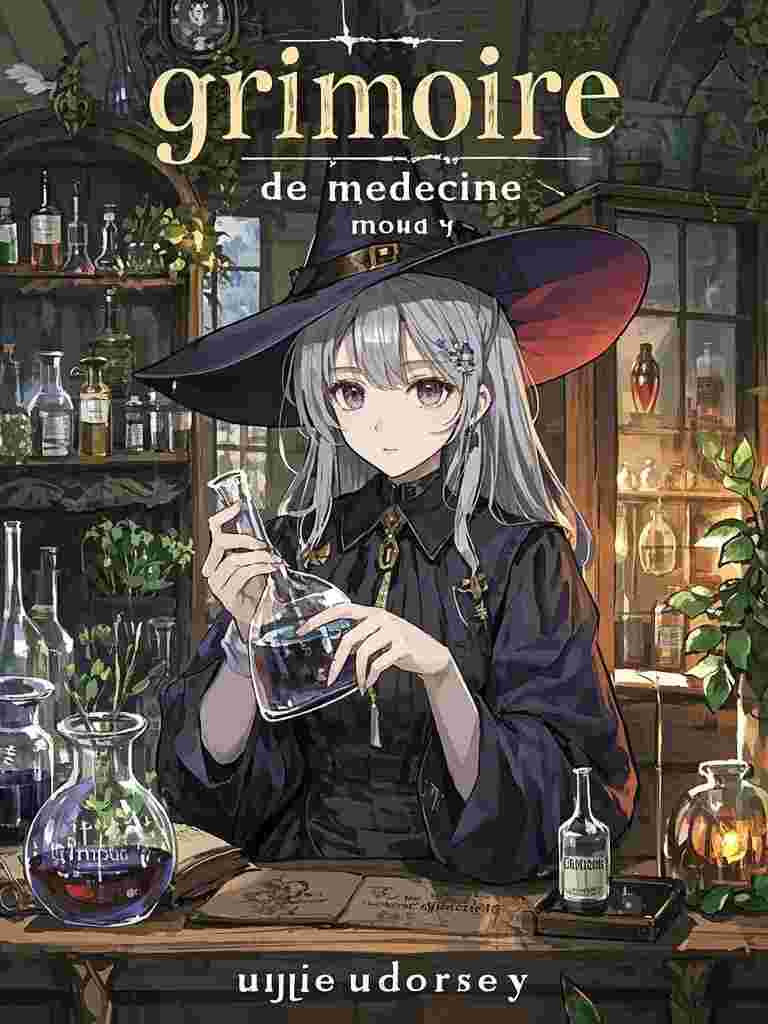!”
一个熟悉又带着惊惶的女声穿透雨幕传来。
苏晚抬起沉重的眼皮,看见同车间的刘玉梅撑着把旧伞,深一脚浅一脚地跑过来,脸上满是惊骇,“这…这是咋弄的?
陈建国那个畜生又……”苏晚想开口,喉咙却只发出嗬嗬的气流声,剧痛让她瞬间白了脸,只能无力地摇摇头。
“别说话!
别说话!”
刘玉梅赶紧蹲下,看着她脖子上缠着的、被雨水和血水浸透的肮脏布条,眼圈一下子就红了,“走,先去厂卫生所!
王大爷,搭把手!”
卫生所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陈旧药品混合的刺鼻气味。
厂医张大夫是个头发花白、面容严肃的老太太,她剪开苏晚脖子上湿透的布条,露出下面那道狰狞的伤口——皮肉外翻,缝线歪歪扭扭,周围红肿发炎,渗着黄水和血丝。
张大夫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一边用镊子夹着沾了酒精的棉球小心清理,一边低声骂:“造孽啊…真是造孽!
下手这么狠,是要人命啊!”
酒精触及伤口的剧痛让苏晚浑身一哆嗦,牙齿死死咬住下唇,尝到了血腥味。
她闭上眼,昨晚那恐怖的死亡预知画面和陈建国扭曲的脸再次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来。
“小苏,”张大夫的声音带着沉沉的叹息,“你这伤…太深了,差点就…唉!
厂里领导也知道了。
保卫科那边……可能会找你问话。”
她顿了顿,压低了声音,“保卫科那个新来的周副科长,听说……挺厉害的。
你说话当心点。”
苏晚的心猛地一沉。
保卫科?
周副科长?
前世模糊的记忆碎片里,似乎有这个名字,一个总是带着职业化微笑,眼神却像鹰隼般锐利冰冷的男人。
清理、换药、重新包扎。
整个过程苏晚都沉默着,像一尊没有生气的泥塑。
喉咙的疼痛和内心的惊涛骇浪让她精疲力竭。
刘玉梅扶着她走出卫生所时,天光已经大亮,雨停了,但天空依旧阴沉得像一块脏抹布。
纺织厂特有的巨大轰鸣声从各个车间传来,空气里漂浮着棉絮和机油的味道。
“晚妹子,别怕。”
刘玉梅用力搀着她,声音带着暖意,“我跟王主任说了,你先去仓库那边清点下新来的棉纱包,活儿轻省点,离那些机器也远。
养好伤再说!”
她顿了顿,又小声补充,“王主任人

我看见凶手在发光苏晚陈建国后续+全文
推荐指数:10分
长篇现代言情《我看见凶手在发光苏晚陈建国后续+全文》,男女主角苏晚陈建国身边发生的故事精彩纷呈,非常值得一读,作者“无蔗糖兔子”所著,主要讲述的是:冰冷的雨水砸在脸上,带着初冬特有的、铁锈般的腥气。苏晚猛地睁开眼,视线被粘稠的黑暗和更粘稠的液体糊住。每一次微弱的呼吸都拉扯着脖颈深处一道锯齿状的剧痛,像有无数烧红的钢针在那里反复穿刺、缝合。她艰难地转动眼球,浑浊的瞳孔里映出头顶那盏昏黄摇曳的灯泡,灯丝苟延残喘地发出嗞嗞微响。意识如同沉船碎片,一点......
第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