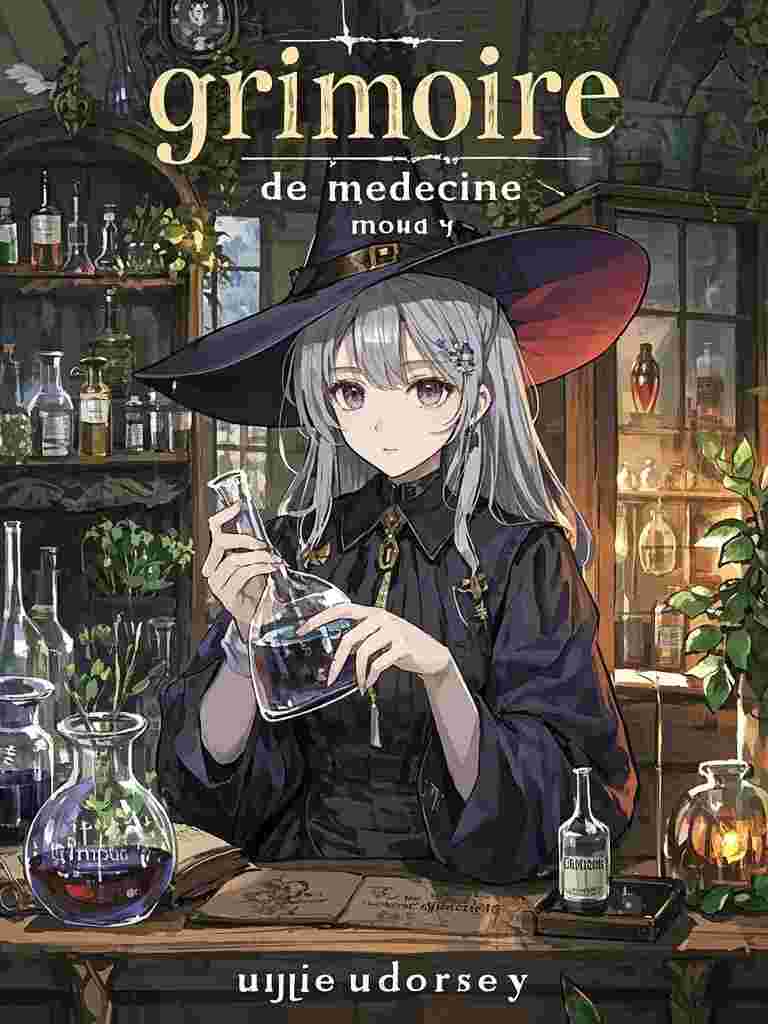一片空白,巨大的惊恐如同海啸般将我淹没,几乎站立不稳。
牌位……我的名字刻在牌位上……棺材……嘉树在里面?
他已经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婆婆这几天让我照顾的……是什么?
一个更加恐怖绝伦的念头攫住了我:婆婆肩窝下流出的……那真的是血吗?
那粘稠的、暗红的颜色……“嗬……嗬……”身后,那如同破风箱般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种令人牙酸的摩擦感,越来越近!
我猛地回头!
婆婆就站在储物间的门口!
烛光从她身后打来,将她佝偻的影子拉得巨大而扭曲,投射在堆满纸扎的墙壁上,像一头择人而噬的怪物。
她的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冰冷和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空洞的执着。
肩窝下,那把剪刀还插在那里,暗红色的“液体”依旧在缓慢地渗出,染红了她大片紫色的衣襟。
但她似乎……感觉不到疼痛?
她的目光,越过我,死死地钉在那口敞开的棺材上,喉咙里持续发出“嗬……嗬……”的声音。
然后,她极其缓慢地、动作僵硬地抬起那只没有受伤的手,再次指向棺材,干裂的嘴唇翕动着,终于挤出了几个破碎而诡异的音节:“吉……时……到……了……去……拜……堂……”她的声音嘶哑得如同砂纸摩擦,每一个字都带着坟墓里的阴冷气息。
“拜堂?”
我失声尖叫,声音因为极致的恐惧而扭曲变调,“跟谁拜堂?
嘉树?
他在棺材里?!”
我浑身抖得像风中的落叶,目光惊恐地在婆婆那张死气沉沉的脸和那口散发着不祥气息的棺材之间来回扫视。
婆婆没有回答。
她那双浑浊空洞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嘴角极其缓慢地、极其僵硬地向上扯动,拉扯出一个非人的、令人头皮炸裂的诡异笑容。
她无视肩窝下插着的剪刀,无视那不断渗出的暗红污渍,像一具被无形丝线牵引的木偶,一步,一步,极其僵硬地朝我逼近。
浓烈的檀香味、血腥味(如果那真的是血的话)、还有棺材散发出的朽木与油漆的混合气味,随着她的靠近,形成一股令人窒息的浊流,狠狠冲击着我的感官。
逃!
必须逃出去!
这个念头如同濒死的呐喊在脑海中炸响。
我不能再待在这

我的冥婚嫁衣王淑芬嘉树后续+全文
推荐指数:10分
现代言情《我的冥婚嫁衣王淑芬嘉树后续+全文》,现已上架,主角是王淑芬嘉树,作者“喜欢亚河豚的鲁大头”大大创作的一部优秀著作,无错版精彩剧情描述:1 血色嫁衣雨点砸在玻璃上,声音密集又沉闷,像无数冰冷的手指在急促地敲打。窗外是泼墨般的浓黑,偶尔一道惨白的闪电撕裂天幕,瞬间照亮被狂风蹂躏得东倒西歪的树影,随即又被更深的黑暗吞没。轰隆的雷声紧随而至,震得窗框都在微微发颤。屋里彻底黑了,停电了。“晚晚啊,别怕别怕!”婆婆王淑芬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带着......
第1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