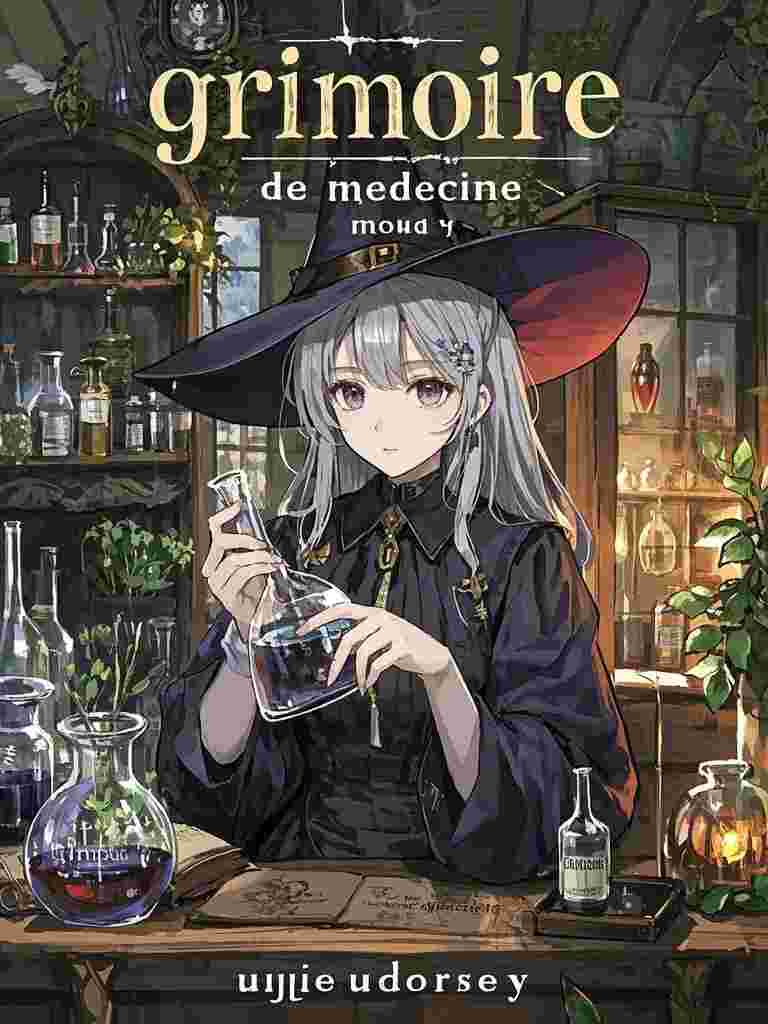身,捻起一撮还带着火星的灰。
灰在他掌心簌簌散开,混着几根蜷曲的焦毛,风一吹,就飘进了谷底的乱石缝里。
他抬头望向谷口,阳光正烈,把士兵们的影子钉在地上,像一排排沉默的界碑。
重机枪的枪管还在发烫,迫击炮的炮口凝着硝烟,山风掠过时,带着火药和烧焦的腥气,盖过了林子里的松香。
“赵旅长,”朱福林的声音不高,却在空旷的谷底里撞出回音,“让弟兄们先撤吧。
这里,我来收拾。”
赵卫东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胳膊。
士兵们列队撤出鹰嘴谷时,脚步放得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最后一个士兵离开时,回头看了眼那堆灰烬,眼里带着点说不清的敬畏——毕竟,他们刚炸碎的,是活了几百年的“仙家”。
谷里只剩朱福林一人。
他从怀里掏出孟根花萨满的蛇头拐杖,把拐杖头轻轻戳进灰烬里,像是在钉一块界碑。
拐杖上的绿石头映着阳光,亮得刺眼。
“黄三太奶,”他对着灰烬说,声音里没了之前的愤怒,只剩一种冷硬的平静,“你总说自己渡过得天雷,说自己护过抗联,说这林子是你的。”
他捻了捻指尖的灰,灰里还掺着点没烧透的骨渣,硌得慌。
“你厉害,能打,能幻化人形,能让萨满为你送命。
可你再厉害,有几个师?”
他笑了笑,笑声里带着点嘲讽,“刚才山头上的迫击炮、重机枪,谷外的山炮,那是一个旅。
你觉得你那点法力,扛得住?”
风卷起灰烬,迷了他的眼。
他抬手抹了把,指尖蹭上黑灰,像给眼眶画了道墨线。
“你记恨砍树的工人,记恨管你的民管局,可你忘了,1938年你护的不是林子,是‘人’。
现在你杀的,也是‘人’。”
他把蛇头拐杖往地上顿了顿,杖头的绿石头磕在焦土上,“规矩就是规矩。
当年你对着镇魂鼓磕头,说‘永不伤善人’,那是规矩;现在你破了规矩,就得受罚,这也是规矩。”
他站起身,把拐杖插进灰烬堆里,让蛇头朝上,像是在让孟根花萨满看着这一切。
“别拿‘仙家’当幌子。”
朱福林最后看了眼那堆灰,转身往谷外走,“忘了护人的本,伤了无辜的命,再大的道行,也不过是披了张人皮的畜牲。”
风穿过谷底,

仙家?仙家几个师啊番外
推荐指数:10分
无删减版本的现代言情《仙家?仙家几个师啊番外》,成功收获了一大批的读者们关注,故事的原创作者叫做苦下,非常的具有实力,主角黄仙王建军。简要概述:1989年的秋老虎,把大兴安岭的林子蒸得像口密不透风的大蒸笼。空气里飘着松针腐烂的酸气,混着伐木场停工后汽油的味道,吸进肺里,又闷又沉。老周蹲在鹰嘴崖的崖边,烟卷烧到了手指头,烫得他猛地一哆嗦,才发现自己盯着沟底那两具尸体,已经看了快一个钟头。“他娘的,邪门,真邪门。”老周把烟蒂往地上一摁,唾沫啐在......
第1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