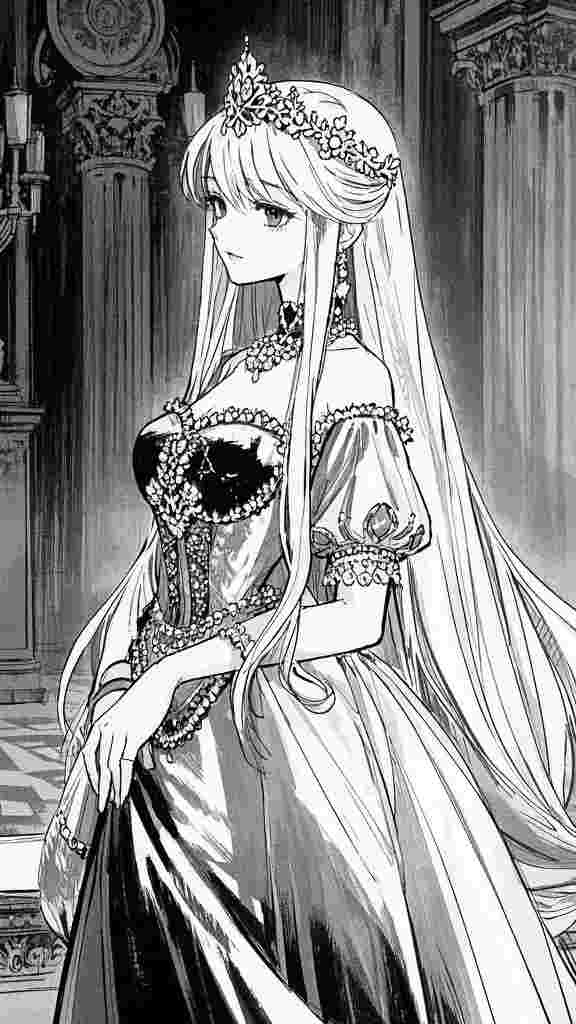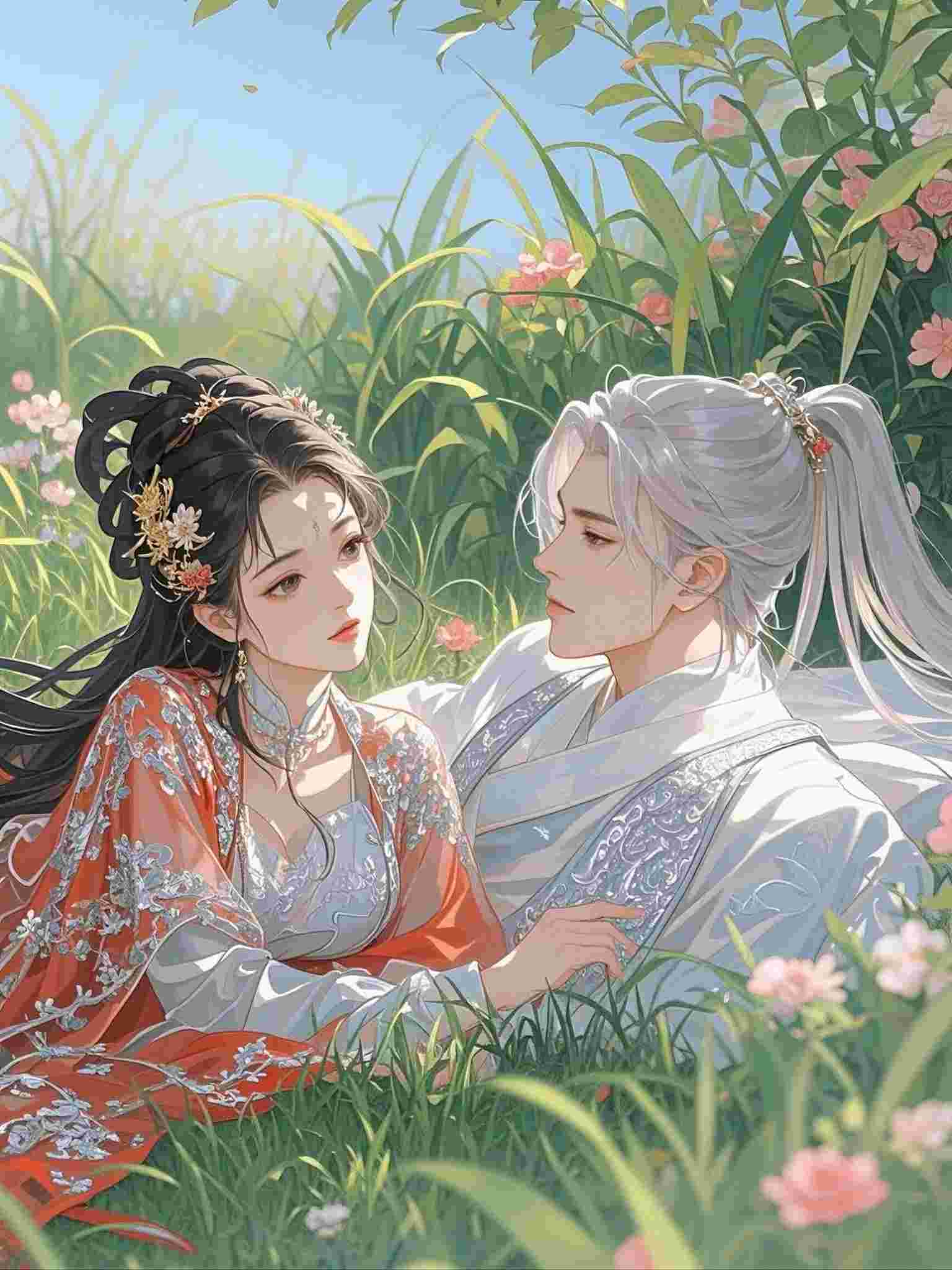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用手帕小心翼翼包裹着的东西。
他打开手帕,里面是一块摔得变了形的军用怀表。
表的指针,永远地停在了一个时刻。
表的背面,刻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
那字,是用刀尖,或者别的什么尖锐的东西,一下一下刻上去的。
字迹很浅,几乎快要看不清。
我凑近了,辨认了很久,才终于看清了那几个字——“雪梅,等我。”
我的眼泪,再一次决堤。
原来,海边的风,真的吹上了雪山顶。
只是,等我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07我最终还是没能去成西疆。
那场高烧,加上巨大的精神打击,让我的身体彻底垮了。
我在卫生院躺了半个多月才缓过来。
这期间,李主任和那位军官来看过我几次。
陈红和张桂兰的案子已经查清了。
陈红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陈卫东的,而是她在县城里认识的一个小混混的。
她得知陈卫东牺牲的消息后,就动了歪心思,想来一招狸猫换太子。
张桂兰则是利欲熏心,为了儿子的抚恤金和那份“烈士家属”的荣耀,选择跟陈红同流合污。
最终,陈红因诈骗罪、伪造公文罪,被判了十年。
张桂兰因为是从犯,年纪也大了,判了三年,缓期执行。
陈家,彻底倒了。
陈卫国,那个打了我一巴掌的男人,也被单位开除了。
他们都付出了代价。
可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出院那天,军官来接我。
他告诉我,部队给我安排了住处,就在县城的军区家属院。
陈卫东的抚恤金和遗物,也都一并交给了我。
我成了一名烈士遗孀。
我住进了一个小小的单间,房间不大,但很干净。
墙上,挂着一张陈卫东的二等功奖状。
我把那块摔坏的怀表,放在了奖状下面。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我开始很少说话,每天就是对着那张奖状和怀表发呆。
我时常在想,陈卫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刻下那行字的时候,在想什么?
他是不是也曾无数次地想象过我的样子?
我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隔着阴阳两界,却因为这一场荒唐的婚姻,和一块破碎的怀表,产生了某种奇特的联结。
我开始给他写信。
就像以前一样,把信写好,装进信封,写上那个我再也无法寄达的地址。
然后,把信一

海风吹暖雪山之巅完结+番外
推荐指数:10分
现代言情《海风吹暖雪山之巅完结+番外》,现已完结,主要人物是陈卫东陈红,文章的原创作者叫做“拉拉圈”,非常的有看点,小说精彩剧情讲述的是:嫁给全军区的活英雄陈卫东那天,我没见过他。只收到他托人带来的一句话:“等我回来,给你挣个凤冠霞帔。”可我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报告,和他表妹挺着肚子上门。她说,她肚子里的,才是陈卫东的种。所有人都劝我认命,一个乡下孤女,配不上雪山顶上的苍鹰。可他们不知道,我这只燕子,也能飞上雪山,掀翻他们的天。01“......
第1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