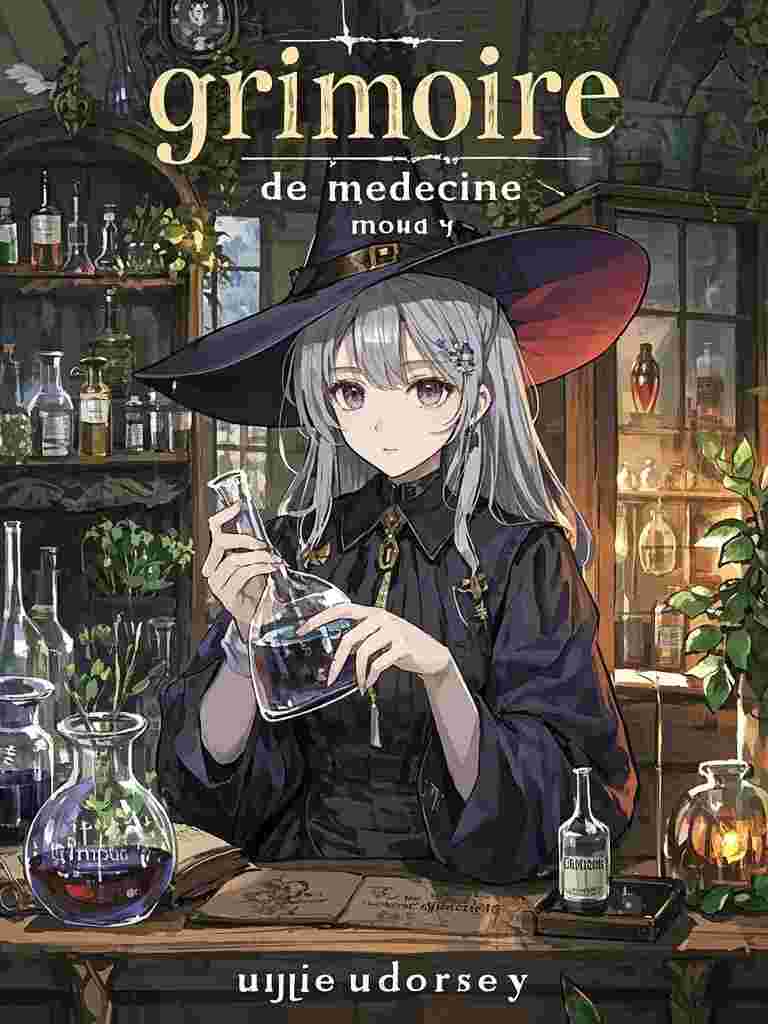日,他红衣猎猎,笑靥如花。
如今,几道狰狞的伤疤爬过眉骨,在眼下刻出深深的沟壑,那是风沙与刀刃留下的印记。
可即便如此,他紧抿的唇角仍透着一股不屈的倔强,像是哪怕入了黄泉,也不肯低下半分头颅。
辛愿的目光缓缓下移,落在他交握的双手上。
那双手曾为她摘过海棠,为她研过墨,为她牵过马儿,此刻却伤痕累累,布满冻疮,僵硬地蜷着,指节泛白,死死攥一枚磨得光滑的平安扣。
是那枚她出征前塞给她的玉佩。
那枚玉佩,她自出生时就带在身边,保了她十几年的平安,为何保不了她夫君的平安?
她伸出手,指尖轻轻拂过他冰冷的脸颊。
那些伤疤硌得她心疼,她想抚平它们,想问问他疼不疼,可他再也不会回答了。
眼泪终于决堤,大颗大颗砸在他的衣襟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却暖不了那彻骨的寒凉。
“啊朝.....”她的声音哽咽着,像被砂纸打磨过般沙哑“你不是说过,要同我做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夫妻,要同我共白首,你怎么怎么……”她不顾阻拦,不顾寒铁甲胄硌得生疼,探入半个身子,将冰冷的身躯死死搂进怀里。
发间珠钗散落,撞在棺木上发出清响,混着压抑的哭声在风雪里碎成齑粉。
绣着并蒂莲的帕子徒劳擦拭他凝固的血迹,染得通红的指尖却怎么也暖不化他渐渐僵硬的面容。
远处传来丧钟悲鸣,她却恍若未闻,只是一遍又一遍亲吻他结着冰晶的眉眼,仿佛这样就能唤醒沉睡的人。
风雪越卷越急,很快将相拥的身影覆上厚厚的素白,唯有断续的抽噎声,融进苍茫天地间,成了这场寒雪里最凄厉的挽歌。
此时,岐朝意身边亲信递上一封信,牛皮纸被血浸染大半,辛愿指间触到纸页,像触到寒冰。
展开开时,手止不住的颤抖。
《与妻书》吾妻见字如吾,朔风裹着硝烟漫过军旗时,我攥着你送的平安扣,忽觉唇齿间尽是江南梅雨季的潮湿。
那年杏花微雨,你踏过青石板扑进我怀里,鬓边的茉莉沾了我半襟香,竟比此刻塞外的月光还要清亮。
箭雨破空的轰鸣中,我恍惚又见你倚在回廊下等我归家。
案头的《长干行》翻到“十六君远行”那页,墨迹被茶渍晕染

意许千愿岐朝意青梅:结局+番外+完结
推荐指数:10分
现代言情《意许千愿岐朝意青梅:结局+番外+完结》是作者“松棠容与”诚意出品的一部燃情之作,岐朝意青梅两位主角之间故事值得细细品读,主要讲述的是:1 青梅绕床 红烛映窗“平安,待我平定北疆收复失地,我们便做一对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夫妻”“平安,等我”辛愿的名字是父亲取的,愿,是心愿,是期许;字平安,是兄长求来的,盼她一生顺遂无虞。她出生那日,京城落了场罕见的大雪,鹅毛般的雪片连下三日,将整座皇城裹得银白,仿佛天地间只剩下纯粹的白。可自那以后,京城......
第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