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泛黄的戏单,上面印着个旦角的黑白照片,眉眼间竟和老爷子此刻的神情有几分相似。
“李老板,当年的事早就了了。”
沈惊鸿把戏单递过去,“张大爷守着您的戏服和头面过了一辈子,临终前还念叨着要把您的牌位请回家。”
老爷子——或者说附身在他身上的戏子,颤抖着接过戏单,指尖抚过照片上的名字,突然“哇”地一声哭出来,哭声凄厉得像老唱片卡了壳。
林砚秋看得怔住,直到沈惊鸿碰了碰她的胳膊:“帮忙搭把手。”
两人把“老爷子”扶到沙发上,沈惊鸿捏着黄符绕着他走了三圈,嘴里念念有词。
符纸燃尽时,老人突然瘫软下去,恢复了原本的平静。
雨还在下,林砚秋给老人整理寿衣的褶皱,沈惊鸿蹲在旁边烧戏单,火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
她忍不住问。
“猜的。”
沈惊鸿笑得狡黠,“罗盘指针转得那么急,怨气里还带着脂粉香,不是戏子是什么?
再说张大爷屋里摆着那么多戏服,obvious(很明显)。”
林砚秋看着他用树枝拨弄火堆,忽然发现他手腕内侧有道浅疤,像被什么东西咬过。
她想起自己左手虎口处的烫伤,是第一次独立处理遗体时,被打翻的烛台烫的。
“多谢。”
她低声说,和上次在停灵堂一样。
沈惊鸿抬头看她,雨珠从屋檐滴落,在他睫毛上凝成细小的水珠:“林小姐,老说谢多生分。
要不,请我吃碗面?”
她没理他,却在心里记下了这句话。
---三三清观的后院有棵老槐树,树下摆着张石桌。
林砚秋第二次来的时候,沈惊鸿正蹲在石桌上画符,黄符纸铺了满桌,朱砂在他指尖晕开,像一朵朵细小的血花。
“你这观里,香火不太旺啊。”
她打量着落满灰尘的供桌,案上的三清像嘴角结着蜘蛛网。
“随缘。”
沈惊鸿头也不抬,笔锋一转,在符纸末端画了个圈,“来都来了,帮我把那边的符纸晾上。”
林砚秋拿起穿好红线的符纸,挂在晾衣绳上。
风一吹,黄符纸哗啦啦地响,像无数只振翅的蝴蝶。
她看着沈惊鸿在石桌上忙碌,阳光透过槐树叶落在他身上,道袍上的灰尘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为什么做道士?”
她突然问。
沈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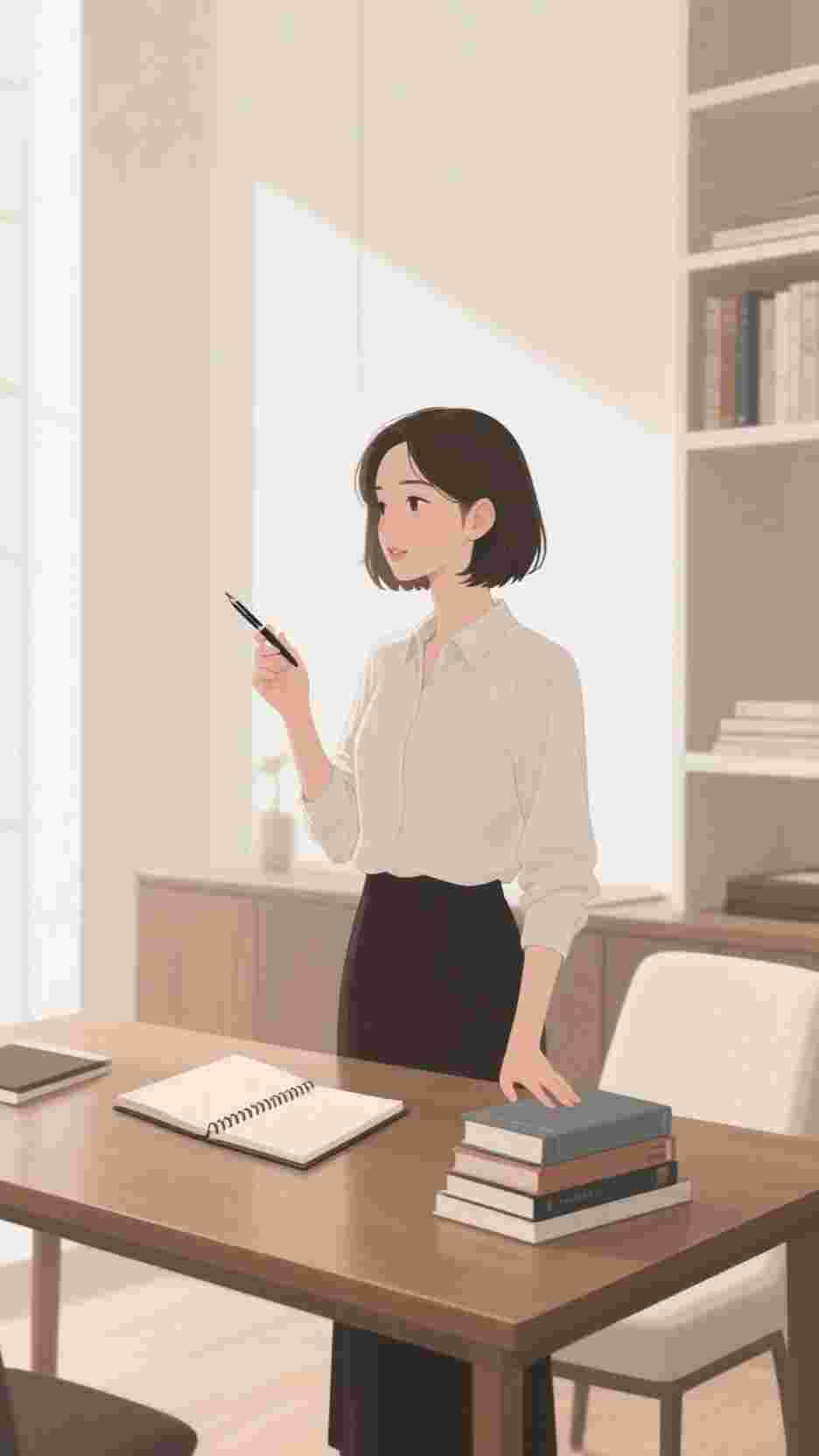
棺前月下:结局+番外+完结
推荐指数:10分
《棺前月下:结局+番外+完结》这本书大家都在找,其实这是一本给力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林砚秋沈惊鸿,讲述了入殓师×道士“让这只鬼从我的顾客身上下来!!!”“附身而已,莫慌~”一林砚秋第一次见到沈惊鸿,是在城郊那间爬满青藤的停灵堂。那日清晨,天光未明,细雨如丝,湿漉漉地贴在屋檐上,顺着斑驳的灰墙滑落。停灵堂孤零零地立在荒草丛生的坟地边缘,像一座被遗忘的庙宇。铁门半掩,门轴发出锈蚀的呻吟,惊起几只栖在屋脊上......
第4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