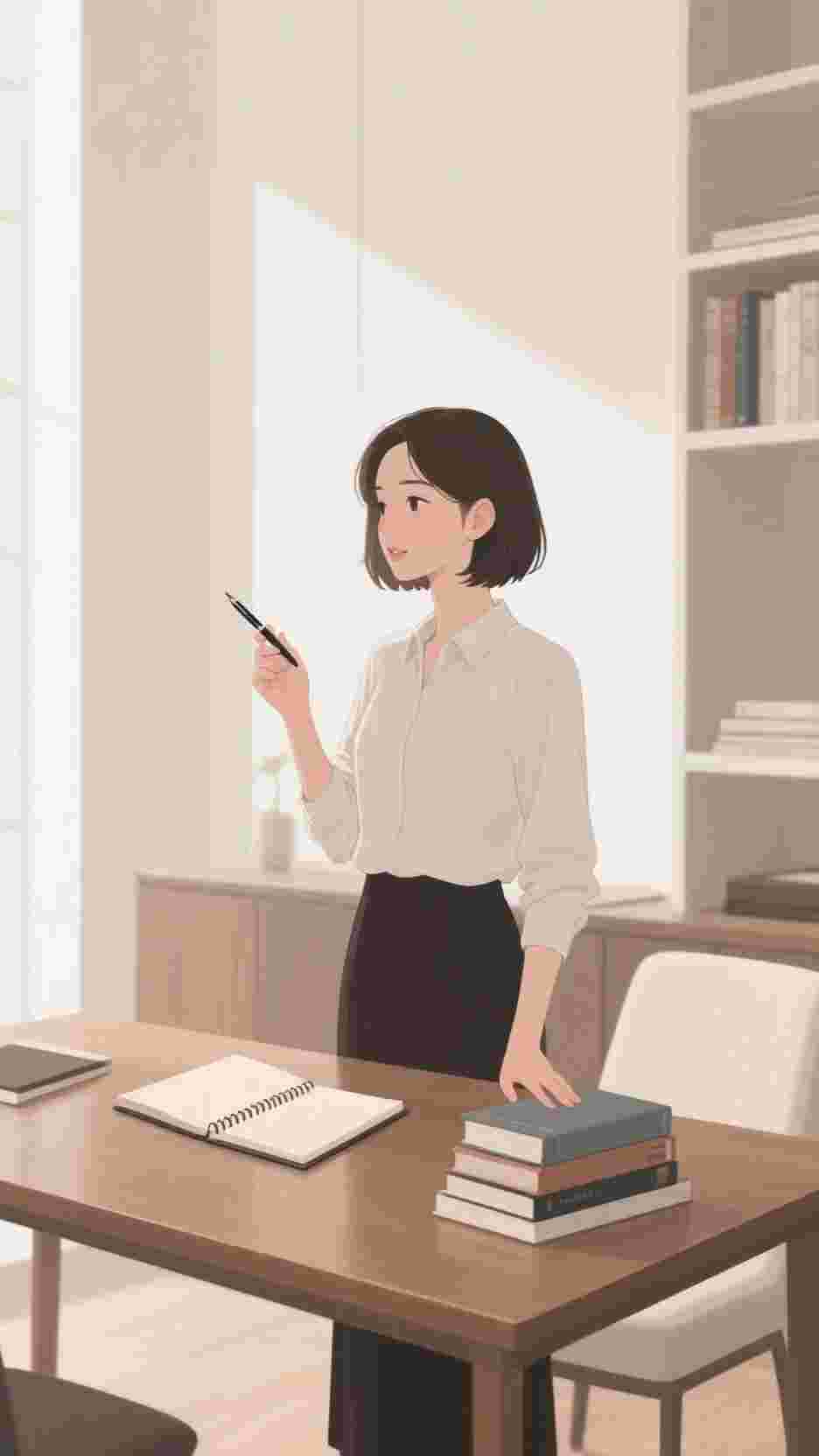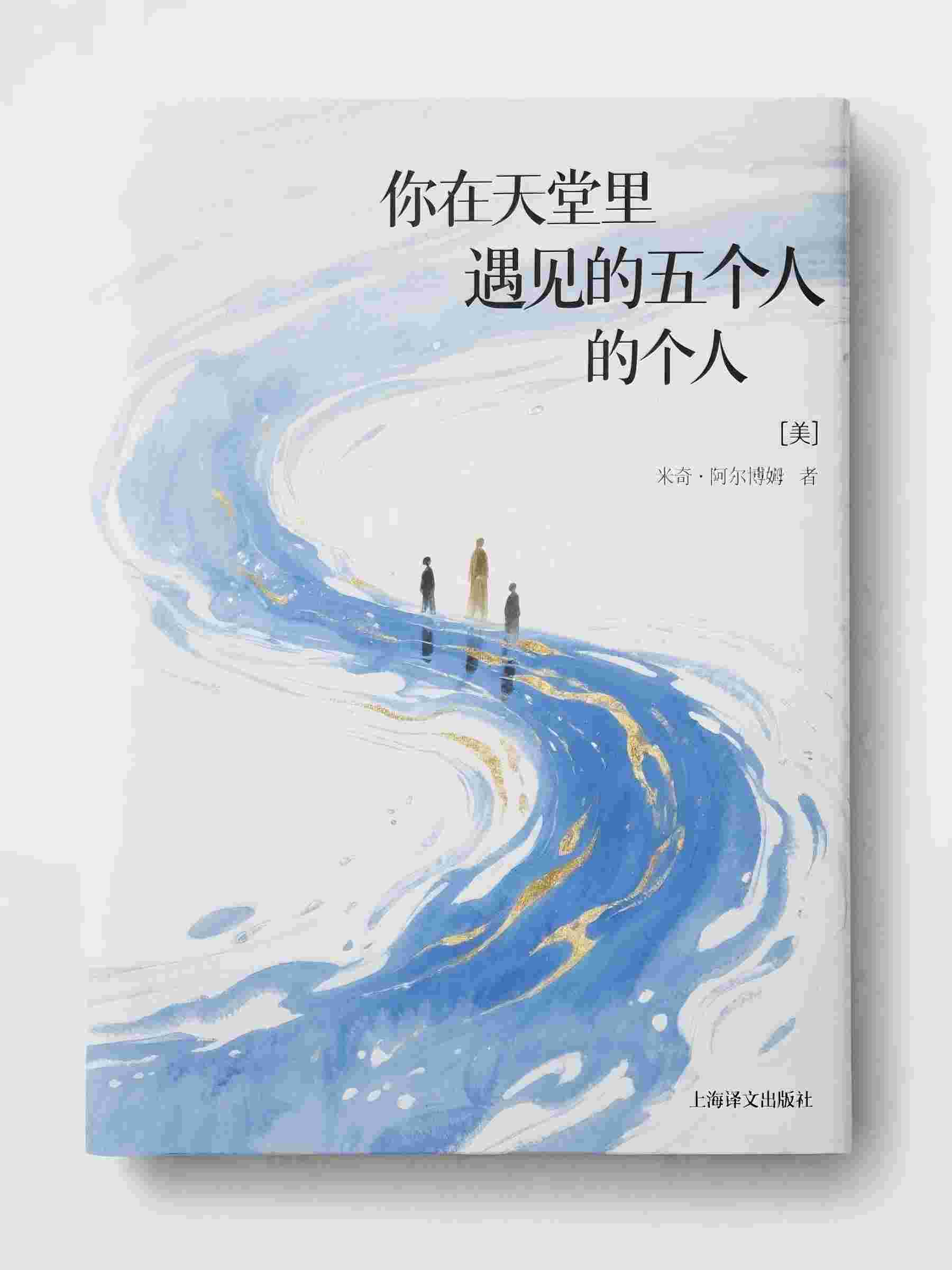万岁千岁。
礼炮轰鸣时,我看见他袖口的龙纹在阳光下闪着冷光,而我凤袍上的凤凰,翅膀尖沾着昨夜不小心蹭上的血——是试图反抗的宫女的血,被内侍用锦帕擦掉了,却还是留下点暗红的渍。
回宫的马车上,他突然靠过来,头抵着我的肩。
龙涎香混着淡淡的血腥气,是他身上从不曾变过的味道。
“他们说,”他的声音发颤,像个怕黑的孩子,“我们是黑龙恶凤,是乱世里催命的煞星。”
我抬手,替他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龙袍。
“那又如何?”
马车碾过青石路,发出沉闷的响,“你我手上的血,早就够染红这龙凤袍了。”
他突然笑了,笑声里带着些释然,又有些说不清的悲凉。
“婉娘,”他抓住我的手,按在他心口的位置,那里的龙纹下,心跳得又沉又稳,“这样,是不是就没人能再分开我们了?”
我望着车窗外掠过的宫墙,那些朱红的墙皮里,不知埋了多少白骨。
大郎的,二郎的,还有那些死在箭下、刀下、火海里的无名魂灵。
他们没能等到的太平,终究被我们踩在了脚下。
“是。”
我轻声说,指尖划过他龙袍上最锋利的一道金线,“从此我们是黑龙恶凤,是这天下的王与后,是彼此唯一的牵绊,也是彼此永远的枷锁。”
马车驶进永巷时,墙角的牵牛花正开得艳。
紫的,蓝的,缠着宫墙往上爬,像极了当年城南小院的模样。
只是这宫里的花,开得再盛,也带着股挥不去的戾气——就像我和他,终究活成了最不想成为的样子,却在这染血的权位上,找到了另一种共生的方式。
他是黑龙,我是恶凤。
我们曾是彼此的光,如今是彼此的影。
这天下是我们的棋盘,也是我们的囚笼,而我们,终将在这方寸之间,纠缠至死。
我与阿砚同掌天下的第十年,宫里的牵牛花爬满了整面宫墙。
紫的、蓝的,在明黄琉璃瓦下疯长,像极了当年城南小院那片泼泼洒洒的生机,只是花藤深处,总藏着些说不清的冷意。
那年冬,北疆传来急报,旧部叛乱,声称要“清君侧,诛恶凤”。
阿砚摔了奏疏,龙涎香在暖炉里烧得发焦。
“他们怕的从来不是我,”他盯着我腕上那只素银镯子——那是用当年绑我的铁链融了

城南花,帝阙血阿砚二郎前文+后续
推荐指数:10分
现代言情《城南花,帝阙血阿砚二郎前文+后续》是由作者“文正字清”创作编写,书中主人公是阿砚二郎,其中内容简介:红烛的蜡油滴在描金的喜字上时,我总爱盯着看。阿砚说那像极了战场上凝固的血,我便拧他的胳膊,骂他满嘴胡吣——那年头,哪有新郎官在洞房里说这个的。他却捉住我的手,往我掌心塞了块暖玉。玉上刻着两只交颈的雁,是他亲手雕的。“婉娘,”他的指腹磨过我掌纹里的薄茧,“等天下太平了,我带你去雁门关外看真正的雁阵,一......
第1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