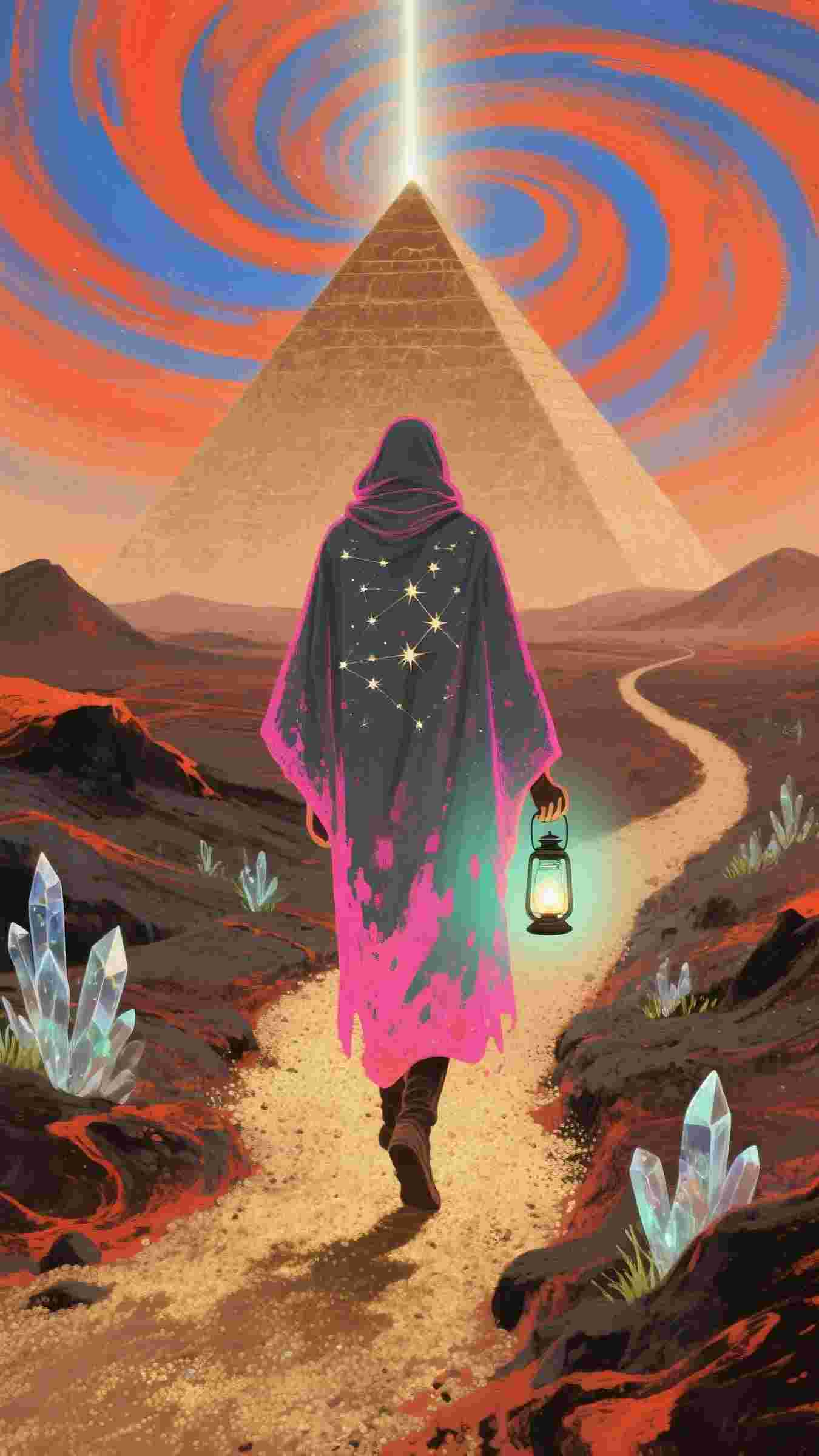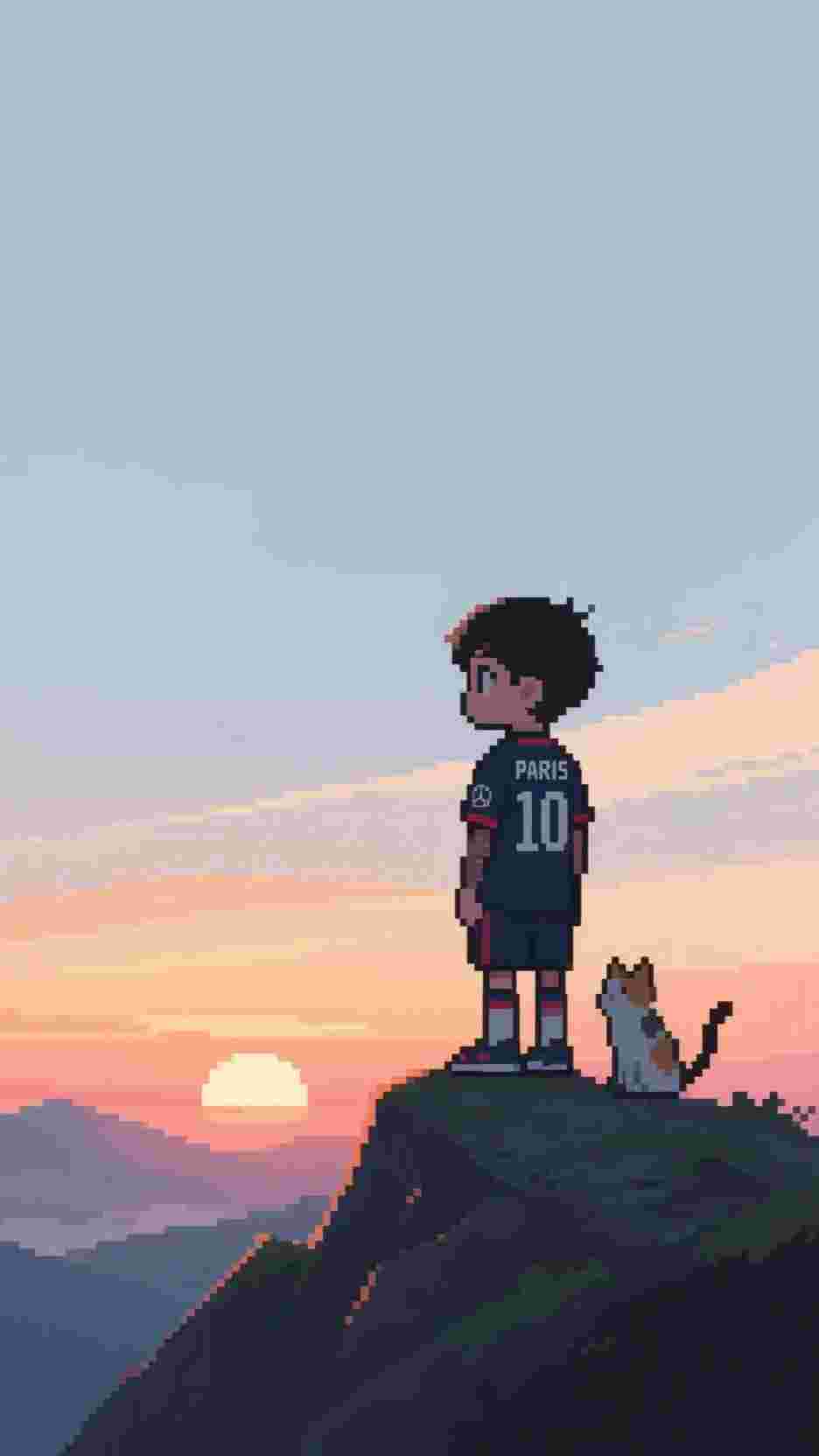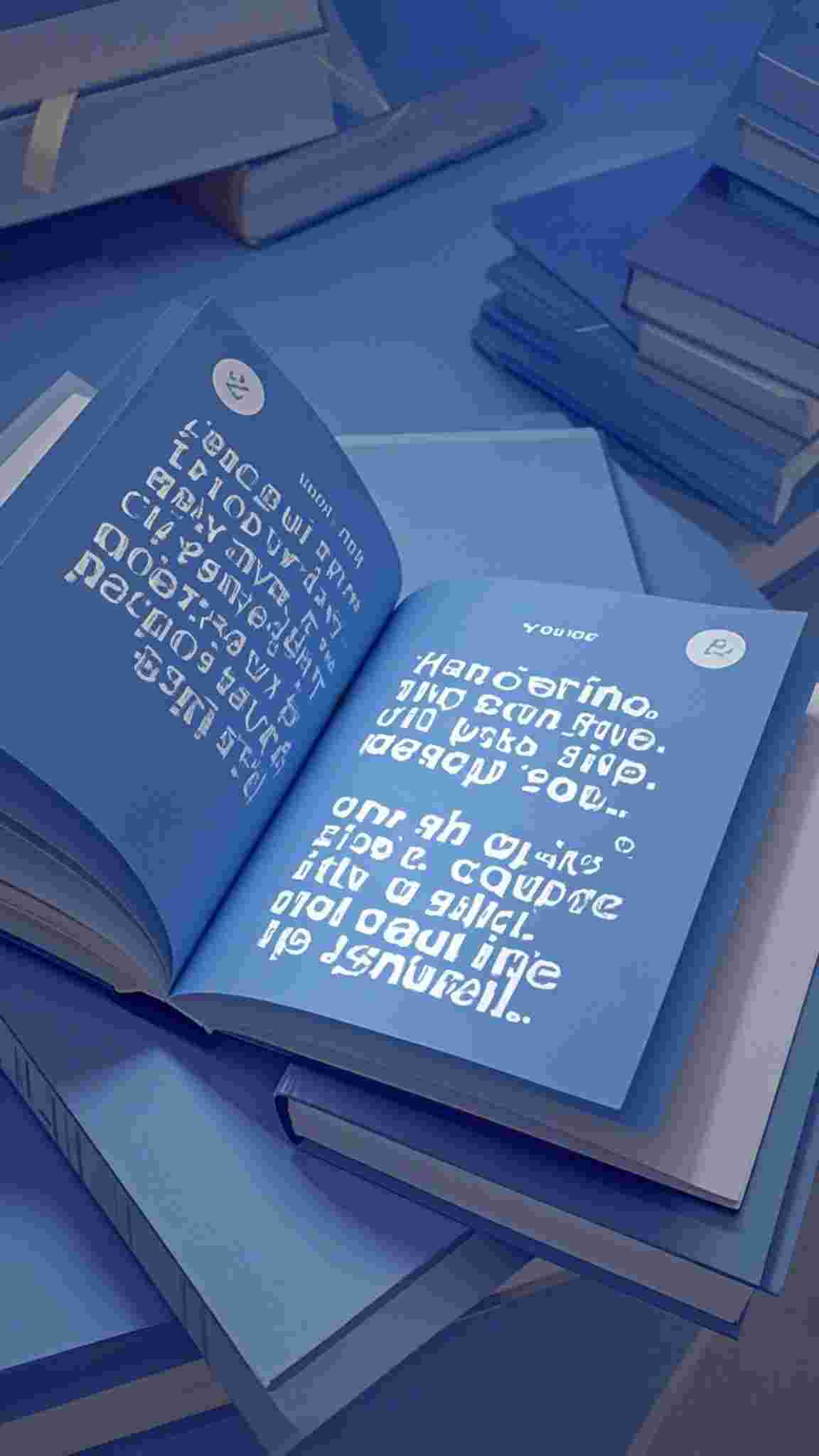江南……去不成了……不去了。”
我握紧他的手,那只曾握过笔、握过剑、也下令放过箭的手,如今冷得像冰,“就在这儿,守着这宫墙,守着这牵牛花,挺好。”
他终究还是走了,在那年的惊蛰。
宫里的牵牛花突然开得格外盛,紫的蓝的,堆在一起,像片翻涌的浪。
新帝是阿砚的侄孙,年纪尚幼,我垂帘听政。
朝臣们暗地里叫我“黑凤太后”,说我眼神里的狠劲,比先皇更甚。
我把那些弹劾我的奏折都留着,装订成册,放在阿砚的龙案上。
每日临朝,我都会穿上那件金线凤袍。
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凤袍上的血迹早已洗尽,只剩下金线在光里流动,像极了当年狼牙关的火。
七十五岁那年,我终于放下了凤印。
新帝已经能独当一面,眼神里有阿砚的冷,也有大郎的烈。
他跪在我面前,问:“太后娘娘,您还有什么嘱咐?”
我指着宫墙的牵牛花,那里的花藤已经爬满了整个宫苑。
“告诉他们,”我说,声音哑得像破旧的风箱,“这天下,是用无数人的命换来的,守不住,就别姓顾。”
弥留之际,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年的洞房。
红烛的蜡油滴在描金的喜字上,阿砚往我手里塞了块暖玉,说:“等天下太平了,带你去看雁阵。”
窗外的牵牛花还在开,紫的蓝的,缠在一起,像两条纠缠至死的龙与凤。
我笑了笑,终于闭上了眼。
原来这一生,争过,恨过,怨过,最终还是和他一起,守着这片用血与骨换来的天下。
我们是黑龙恶凤,是史书里的暴君妖后,可我们心里清楚,我们只是两个没能走到江南的可怜人,守着些不肯忘的念想,活成了彼此的枷锁,也活成了彼此的归宿。
宫墙的牵牛花还在年复一年地开,只是再没人知道,那花藤深处,藏着多少人的名字,多少段没说出口的话。
史官在《大启实录》里写下“黑龙恶凤,共治天下二十载,终成盛世”时,笔尖在“恶”字上顿了顿。
墨滴落在泛黄的纸页上,像极了故宫墙砖缝里渗出的暗红,那是百年雨水也冲不净的痕迹。
后世的学子们总爱争论,顾氏夫妇究竟是乱世枭雄,还是救民水火的真主。
有人说他们屠戮过重,当年青州城破时,三日不封

城南花,帝阙血阿砚二郎:全文+后续+结局
推荐指数:10分
小说《城南花,帝阙血阿砚二郎:全文+后续+结局》新书正在积极地更新中,作者为“文正字清”,主要人物有阿砚二郎,本文精彩内容主要讲述了:红烛的蜡油滴在描金的喜字上时,我总爱盯着看。阿砚说那像极了战场上凝固的血,我便拧他的胳膊,骂他满嘴胡吣——那年头,哪有新郎官在洞房里说这个的。他却捉住我的手,往我掌心塞了块暖玉。玉上刻着两只交颈的雁,是他亲手雕的。“婉娘,”他的指腹磨过我掌纹里的薄茧,“等天下太平了,我带你去雁门关外看真正的雁阵,一......
第1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