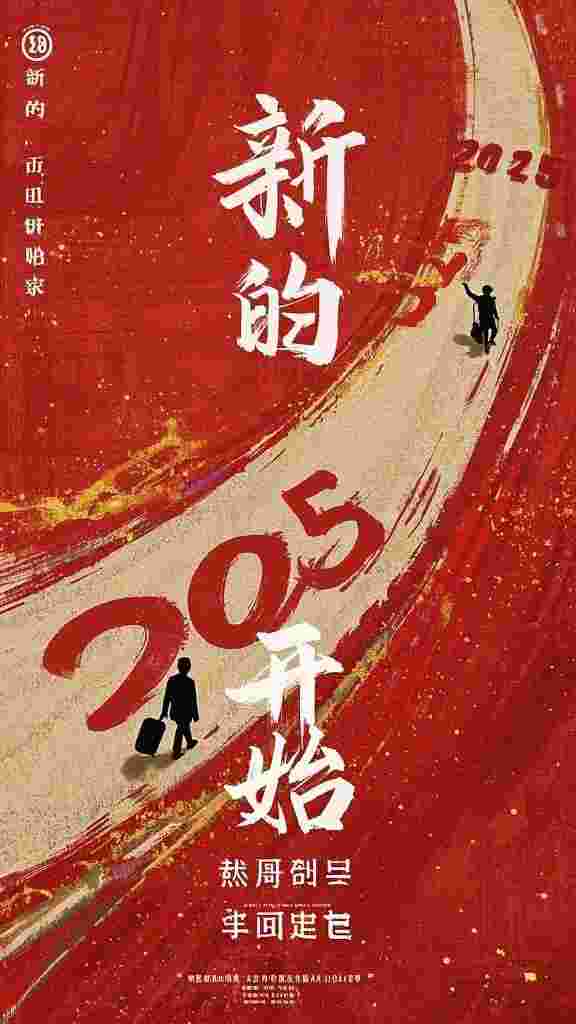在痛……像被剑扎……被火烧……是你的剑……是你的同心佩……它在烧着我……你在罚我是不是?!
你怎么罚都行!
别不见我!
求你……求你……”声音越来越低,带着一种被碾碎了的哽咽,她固执地用双手扒住粗糙冰冷的门板,枯槁的手指几乎要抠进去。
石屋门内一片寂静。
连海风似乎都在这一刻凝固。
只有门外的呜咽绝望,成了这天地间唯一的悲鸣。
不知过了多久。
也许只是一弹指,也许已历千年。
就在沈听蓝的双手因绝望的用力而指甲崩裂、渗出鲜血,人也要沿着门板滑落下去的前一瞬。
石屋内。
没有脚步声。
只有一道极其平淡的、如同隔着万里寒冰层传来的声音,清晰地穿透门板,带着一种恒古不变的寂静,传入门外那几乎崩溃的身影耳中,也落入门口小家伙懵懂的心里:“因果自渡,他人……无咎。”
那声音没有丝毫涟漪,只是平铺直叙一个铁铸般的事实。
仿佛门外那哀绝的哭泣、剜心之痛、疯狂的执念,都与这屋内的空寂无关。
门外扒着门板的那双枯槁的手,猛地僵直!
指尖渗出的鲜血在粗砺的木纹上留下几道蜿蜒的红痕。
那具摇摇欲坠的身体,如同被抽掉了最后一根支撑的朽木,轰然垮塌,顺着门板滑落在地。
她蜷缩在冰冷粗糙的门前,额头死死抵着冰冷刺骨的木门,枯草般的长发凌乱铺散开,整个人剧烈地颤抖着,却再也发不出任何一点声音。
痛?
那曾蚀骨的痛?
此刻早已麻木得毫无感觉。
剩下的,只有一种无穷无尽向下沉沦、如同被整个宇宙抛弃般的冰冷荒芜。
她终于明白,比死亡更冷的,是那道目光下绝对的、永恒的……寂静。
“……道途……”小家伙站在石坪一角,好奇地听着这句从门里传出的话。
他努力挺直了小小的身体,把沾着细沙的手指在衣襟上胡乱擦了擦,然后有样学样地摆出一副自以为“严肃”的表情,奶声奶气地对着那个蜷在门口、仿佛失去了灵魂的女人重复道,带着孩子特有的笨拙和一丝不容置疑的天真:“师爹说啦!
死掉的东西,就别刨出来恶心人啦!”
咣当。
石屋那扇简陋粗糙的木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从里面缓缓地、毫无凝滞

死心后白月光才看清绿茶全文免费
推荐指数:10分
《死心后白月光才看清绿茶全文免费》是作者“多年未梦”的代表作,书中内容围绕主角陆野沈听蓝展开,其中精彩内容是:*这柄含光剑,是我耗尽心血为她炼制的本命灵剑。剑身用的是一块千年难遇的寒月玄铁,剑锷处淬进了一捧稀世罕有的星辰砂,点点微芒流转不息,宛如截下了一片银河嵌在里面。为了这捧星辰砂,我在魔域边缘徘徊近三年,几次差点被混乱的罡风撕碎,才终得以从星辰花上抖落这一点微芒。我记得剑成那日,她初执此剑,眼底星河璀璨......
第3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