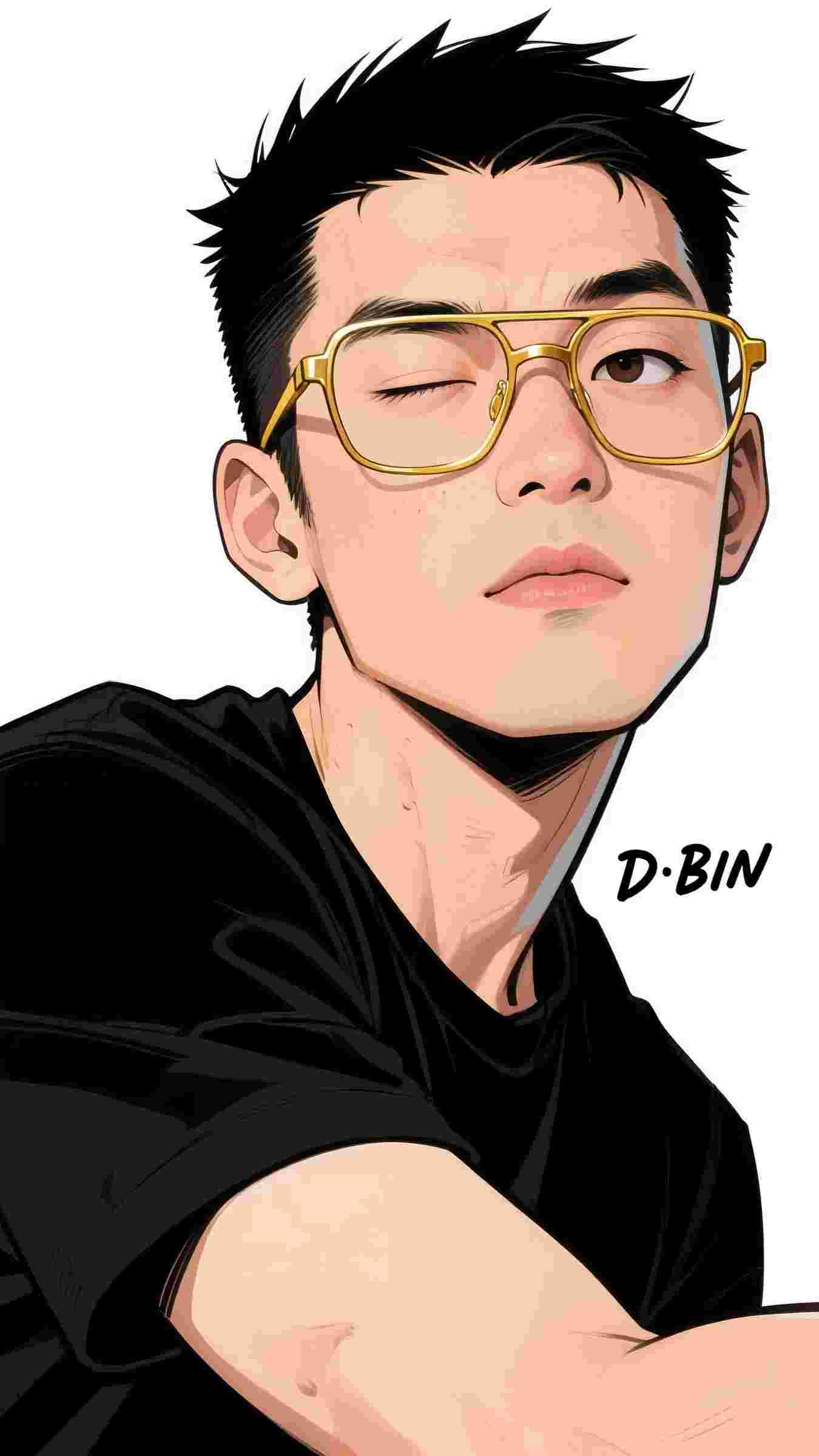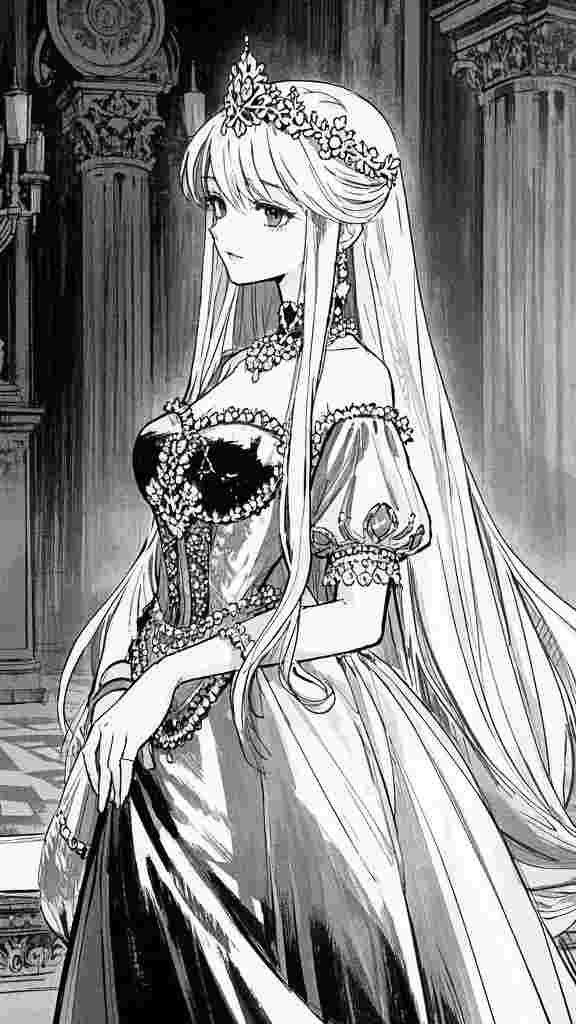垮了我。
我浑身发冷,连站都站不稳了。
就在我即将被这无边的绝望和羞辱彻底淹没的时候,那个一直沉默着的、像雕塑一样的男人,忽然开口了。
陆时川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瞬间切开了这间屋子里令人窒息的空气。
他没有看我,也没有看任何人,他的目光,平静地落在温景行的脸上。
“温叔叔,”他缓缓地问,语气像是在讨论天气,“我记得您是古画修复专家。
十几年前,您修复我父亲收藏的那副《秋山行旅图》时,用的也是这种遇水就无法彻底硬化的特制凝胶,对吗?”
这个问题,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看似微不足道,却瞬间激起了我脑海中的惊天巨浪。
古画修复……凝胶……十几年前……我的父亲!
那支钢笔!
那股阳光炙烤下灰尘混合着旧书的味道!
不是书的味道,是修复古画用的特殊纸张和那种G-7凝胶溶剂混合后,独有的味道!
那支万宝龙钢笔,是温叔叔在我父亲死后“送”给陆时川的遗物!
“浅浅,记住,他们弄错了时间。”
爸爸!
你说的不是案发时间!
你说的……是凝胶硬化的时间!
所有的数据碎片,在那一瞬间,像被一道创世的闪电猛地击中,在我脑中拼接成了一副完整、清晰、又血淋淋的真相图景!
我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温景行那张开始出现裂痕的、温和的脸。
我感觉不到身体的颤抖了,一股冰冷的、燃烧着火焰的力量从我的脊椎升起,贯穿了我的四肢百骸。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冷静得可怕。
“不对。”
我走向白板,拿起那支红色的马克笔,我的手稳得像磐石。
“一切都错了。”
我转身,面对着房间里所有的人,也面对着那个脸色开始发白的男人。
我的独白,开始了。
“第一,凝胶。
林舒的证词里,案发当晚是‘潮湿的雨夜’。
而我父亲发明的G--7凝胶,在湿度超过85%的环境里,永远无法达到‘完全风干硬化’的物理状态。
但我们找到的刀柄上,凝胶却是完全硬化的。
这不是矛盾,这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悖论。
唯一的解释是——这把刀,是在一个极度干燥的环境里被处理好,再被放到储物柜里的。
所谓的‘

我的解剖刀对准新婚丈夫前文+番外
推荐指数:10分
现代言情《我的解剖刀对准新婚丈夫前文+番外》是作者““吟风辞月”诚意出品的一部燃情之作,苏浅陆时川两位主角之间虐恋情深的爱情故事值得细细品读,主要讲述的是:我签的不是婚前协议,是一份有时限的、各怀鬼胎的同盟契约。坐在我对面的男人,陆时川,是我的“新婚丈夫”,更是我恨了许多年的死对头。他将那支昂贵的钢笔推到我面前,动作优雅得像在签署一份价值连城的合同,而不是一场荒唐的婚姻。我知道,他需要我这把全市最锋利的解剖刀,帮他洗刷家族陈年的污点;而我,则需要他这张......
第1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