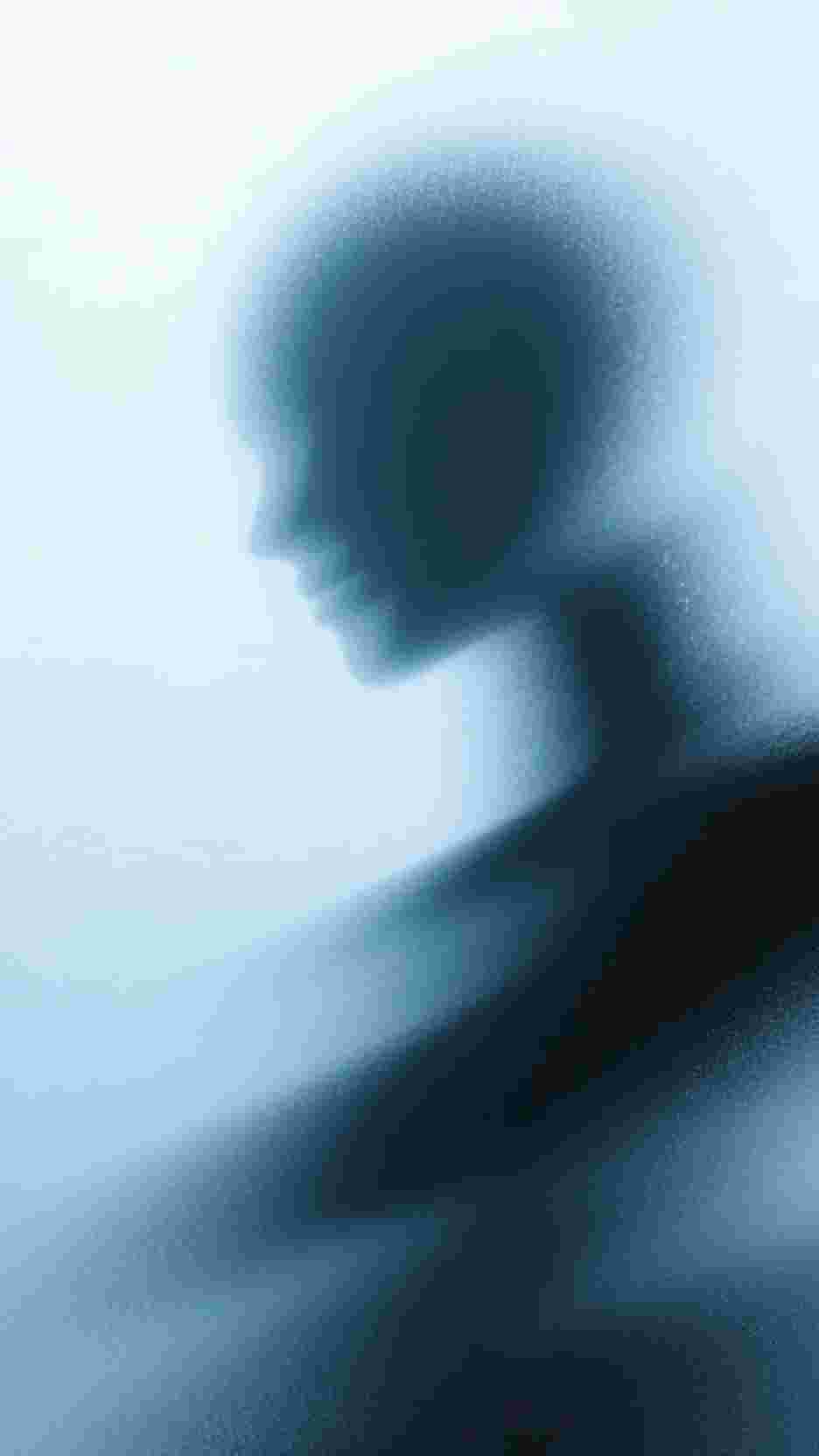有细节、并将“像她”的沈薇带到她面前的心腹的号码。
电话几乎是被瞬间接通。
顾衍之的声音干涩得吓人,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砂纸上磨过,带着一种濒临崩溃的、最后的绝望。
他问:“当年……你们找到沈薇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用尽全身力气,才问出那个足以将他彻底凌迟的问题。
“她是不是……真的不会说话?”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沉默得让顾衍之的心脏,一寸寸沉入冰封的深渊。
许久,那边才传来一声极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回应:“顾总……我们找到沈小姐时……她声带受损,已经……无法发出任何声音了。”
“……无法发出任何声音了……无法发出任何声音了…………”这句话在顾衍之彻底死寂的脑海里疯狂回荡,撞击,撕扯,每一个字都变成了一把生锈的钝刀,反复切割着他的神经。
无法发出声音。
她不是不想说话。
她是……不能。
那个他雇人费尽心机找来的、每一个角度都像极了林婉仪的替身,那个被他按在冰冷的墙上,醉醺醺地逼问“为什么不像她”、“为什么不说话”的女人,她不是沉默,她是失声。
而他,都对她做了什么?
他命令一个哑巴“不准模仿她”说话的神态。
他在一个哑巴比手语解释自己身份时,觉得她识趣。
他对着一个哑巴怒吼“你说话啊!”。
他甚至……因为他记忆中那个活泼健谈、笑声如银铃的婉仪,而憎恶她的死寂。
“嗬……”顾衍之的喉咙里发出一声破碎怪异的气音,像是濒死野兽的哀鸣。
他猛地弯下腰,剧烈的干呕起来,胃里翻江倒海,却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胆汁的苦涩灼烧着喉管。
他想起她签协议时那双过分平静的眼睛。
想起她在花房阳光里,安静修剪枝叶时低垂的睫毛。
想起他朋友调侃时,她抬起手,那双纤细却并不柔美、甚至带着生涩滞感的手,比划出“我只是佣人”时,他心底那丝一闪而过的、被他忽略掉的不适。
那不是识趣,那是……剥开自己鲜血淋漓的尊严,去迎合他定下的、侮辱性的规则。
想起最后一夜,他把她按在墙上,质问她为什么不肯更像一点,为什么眼神那么死气沉沉。
她
总裁的赝品哑妻后颈香:(番外)+(结局) 第9章 试读
爱吃羊肉米饭的土拨鼠 著 白月光沈薇现代言情 来源:cddp 时间:2025-08-22 03:50:31

总裁的赝品哑妻后颈香:(番外)+(结局)
推荐指数:10分
很多朋友很喜欢《总裁的赝品哑妻后颈香:(番外)+(结局)》这部现代言情风格作品,它其实是“爱吃羊肉米饭的土拨鼠”所创作的,内容真实不注水,情感真挚不虚伪,增加了很多精彩的成分,《总裁的赝品哑妻后颈香:(番外)+(结局)》内容概括:他娶我只是因为我像他死去的白月光。 甚至新婚夜就立下规矩:不准公开关系,不准进他卧室,不准模仿她。 我签字点头,遵守所有规则,甚至在他朋友调侃时比手语:「只是佣人。」 那夜他醉酒归来,把我按在墙上:「为什么不像她?你明明可以…」 我沉默着递上离婚协议,他却突然红了眼: 「他们没告诉我…白月光本尊根本......
第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