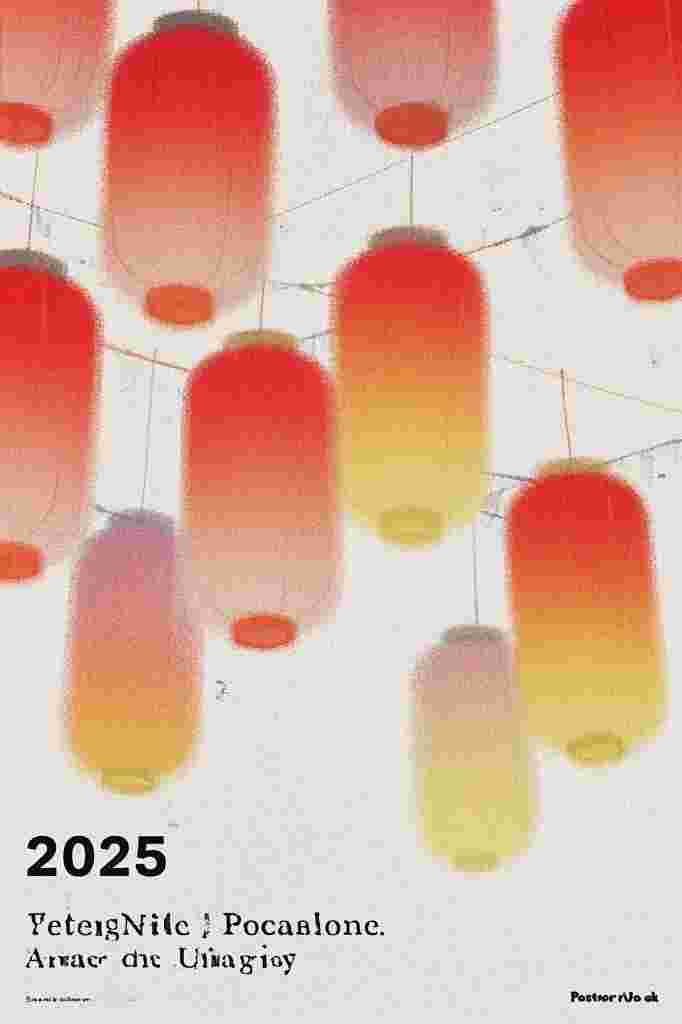“我”,亲手裁决的证据。
“牺牲同伴换取自身安全……”医生的话像毒蛇一样缠绕着我的听觉神经。
胃里又是一阵剧烈的抽搐。
我死死咬住牙关,抵抗着翻涌而上的恶心和眩晕。
屏幕的另一角,陈默——编号001,我的“核心情感变量锚点”——正敏捷地避开一只行动迟缓的丧尸,反手用金属管精准地击打在它的膝关节侧面。
丧尸哀嚎着倒地,他毫不停留,继续向着一个标记为“临时安全屋”的模拟区域移动。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高效、冷静,带着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
程序员?
他曾经告诉我他是后端程序员,整天和代码服务器打交道。
谎言。
一切都是谎言。
从七夕的约会,到那杯温热的奶茶,再到上车前他替我整理鬓发时那句温柔的“别怕,有我”,全都是精心编写的脚本,为了让我这个“设计师”更投入地演好这场“末日求生”的戏码,榨取更极端、更纯粹的情感数据。
愤怒和背叛感像岩浆一样灼烧着我的五脏六腑,反而奇异地压过了那灭顶的恐惧。
颤抖的手指,一点点收拢,握成了拳,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刺痛让我更加清醒。
我不能按下去。
我不能变成他们想要我变成的东西。
至少,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剧本走。
我慢慢抬起头,看向医生。
他依旧微笑着,期待着我被恐惧和压力摧垮,最终屈服于这残酷的“职责”,按下按钮,完成从受害者到加害者的蜕变,成为他们真正的“自己人”。
我深吸了一口冰冷的、带着消毒水气味的空气,努力让声音听起来依旧带着惊惶未定的颤抖,但多了一丝虚弱的妥协:“我……我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这太……突然了。”
医生的笑容加深了,似乎很满意我的“软化”。
他宽容地点点头:“当然,可以理解。
这种认知转换确实需要过程。
不过,时间不等人,实验的窗口期有限。”
他意有所指地瞥向监控屏幕,上面不断有代表“实验体”生命体征的光点在变红、熄灭。
“我能……再看看其他区域的情况吗?”
我怯生生地请求,手指看似无意识地划过平板屏幕,切换着监控视角,“我想了解一下……整体的……进度。”
我的目光躲闪

七夕夜,男友送我进尸笼全本+番外+后续
推荐指数:10分
现代言情《七夕夜,男友送我进尸笼全本+番外+后续》是由作者“润甜甜”创作编写,书中主人公是抖音热门,其中内容简介:七夕当晚的恐怖大巴,实则是人性实验室的筛选工具。醒来后我发现,所有参与者都被植入虚假记忆, 而那个呼唤救命的腐烂丧尸,正是去年被我亲自设计的实验淘汰的前任。最可怕的不是丧尸围城,而是幕后操纵者温柔地擦着我的泪:“别怕,你去年赢得的奖励,就是今年成为新的实验设计师。”我颤抖着看向今年参赛者名单——第一......
第10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