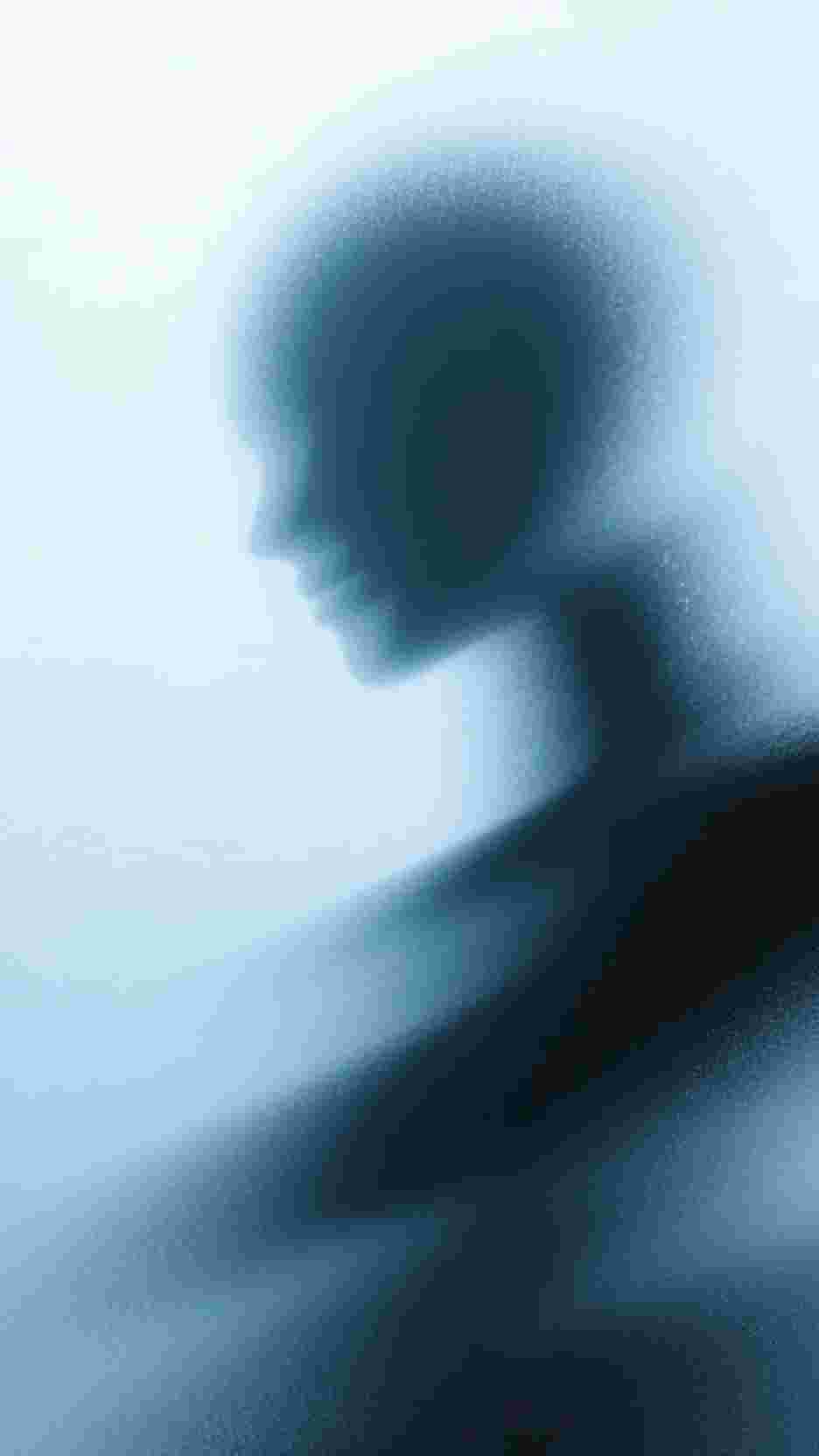你哪个朋友?
他总算有那么一点机灵,愿意把花在棋盘上的时间花在我身上一点。
可前方,医院大门近在咫尺。
你不认识的朋友。
对话框显示了半天"正在输入中"。
我没有再像从前,执着的拿着手机不肯放,等待着平南喻的恩赐般的几句对话。
去后备箱拿起行李。
换好住院服,把手机交给护士时。
我看到平南喻发了条语音。
他说,"楚稚,你喜欢吃的那家披萨店,关门了。"
G国,我拽着他尝过的海鲜披萨,芝士卷边很厚。
我记得,他当时只吃了一口。
他对食物不感兴趣,对我喜欢的更不感兴趣。
怎么会突然记起?
正当我疑惑的皱起眉头时,过长的语音段中传来女声。
吴期远唉声叹气,"好可惜啊。"
我中止了播放,看医生将针头推进小臂,问。
"安乐死的过程会很疼吗?"
戴着口罩的人思考了半晌,他说。
"就像淋了场大雨,不疼,只是全身都很重,湿淋淋的。"
我黯然,那爱平南喻和安静的走向死亡挺像的。
没有眼泪,只有无尽的潮湿。
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
十年,一个人淋雨的滋味我尝够了。
医院双人病房。
一到夜晚就弥漫着有如死寂的安静。
偏偏平南喻的电话就是在这种时候打来的。
执着的,让人无法忽视的长达一分钟的电话铃声。
我接起,是他焦急到失态的语气。"

难逾无弹窗
推荐指数:10分
《难逾》是作者“见青”独家创作上线的一部现代言情,文里出场的灵魂人物分别为平南喻楚稚,超爽情节主要讲述的是:平南喻被誉为天才棋手,我没名没份的陪了他十年。可他升九段时,还是没解出抓周时抓的那张残谱。「按照规矩,没解出残谱我不能娶妻,抱歉。」我没有跟他闹,安静的帮他整理出国的行李,祝他比赛顺利。他不知道,他在异国大放光彩的那一刻。我正要签下自己的安乐死协议。...
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