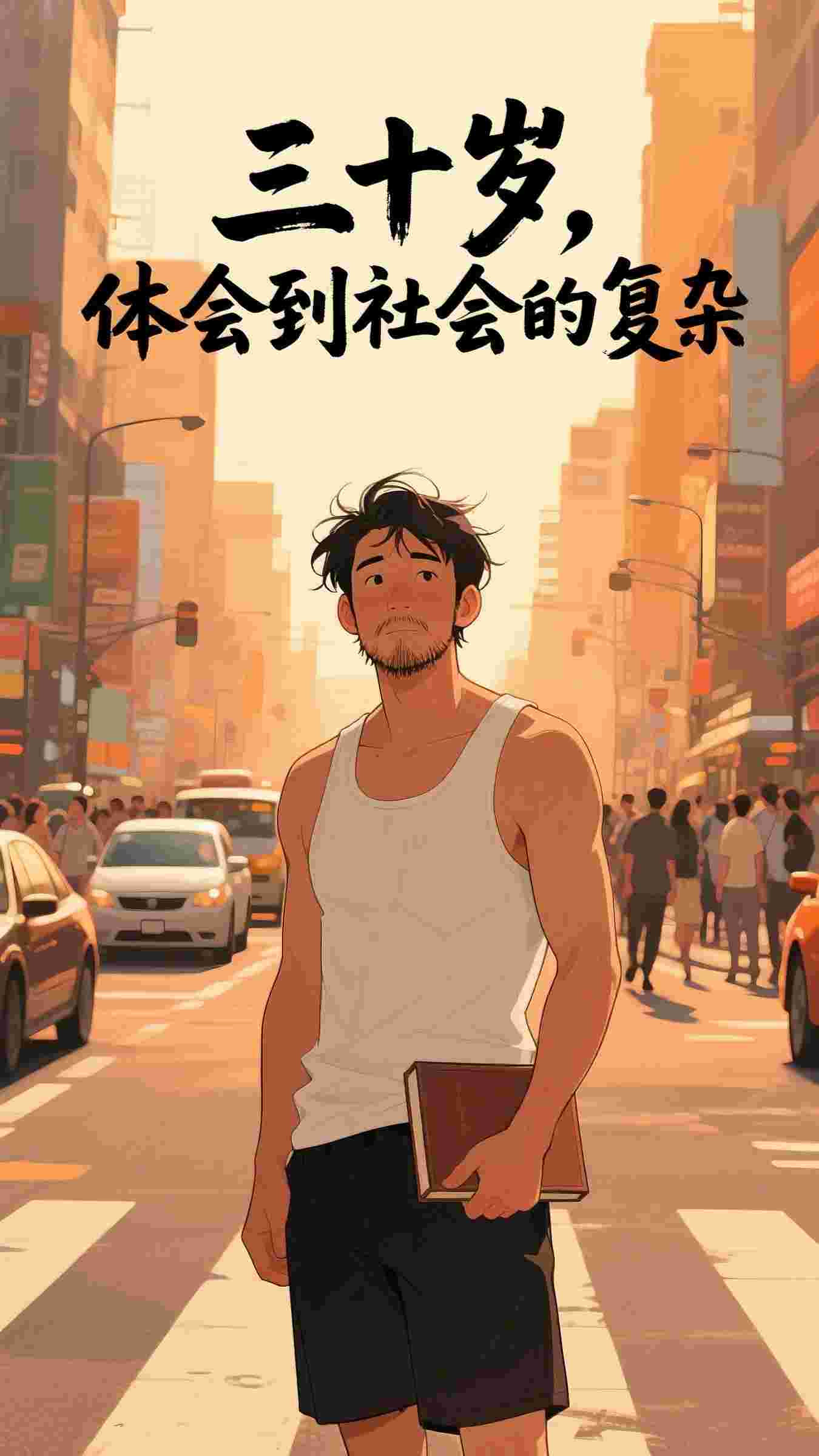疼。
送来的晚饭是半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冷馒头和一碗看不见米粒的稀粥。
夜里,她和其他几个低等丫鬟挤在一间四处漏风的通铺屋里,被子又薄又硬,带着一股难闻的霉味。
她蜷缩在冰冷的被窝里,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身体疲惫到了极点,意识却清醒得可怕。
裴衍之的脸,那双冰冷审视的眼睛,总在她闭上眼时浮现。
这不是结束,只是开始。
她知道。
他在磨她,用这种方式告诉她,留在他身边,哪怕是做最低等的奴婢,也比她想象的要难上千百倍。
接下来的日子,重复着同样的煎熬。
无尽的冰冷衣物,粗糙的食物,刻薄的管事嬷嬷时不时的刁难和斥骂。
她沉默地承受着,像个没有知觉的木偶,只是机械地搓洗、漂净、晾晒。
偶尔,她会在送洗好的衣物去主院时,远远看到裴衍之。
有时他正出门,披着墨色大氅,身形挺拔,步履生风,一群属官恭敬地跟在身后,他侧耳听着汇报,神色冷峻,一个眼神扫过,便让人噤若寒蝉。
他从不会看向洗衣房的方向,仿佛那日收留她,只是随手丢开一件微不足道的垃圾。
她就像一粒尘埃,无声无息地漂浮在他庞大府邸的最边缘。
他给她生存的缝隙,却又用最磨人的方式提醒她她的身份和代价。
直到那日午后。
4沈知微被管事嬷嬷叫去,责令她将一批新到的贵重丝绸面料送去绣房。
这些面料是江南新贡的软烟罗,轻薄如烟,价值千金,专供裴衍之制作春衣。
她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叠光滑冰凉的布料,穿过花园的九曲回廊。
她低着头,尽量避让人。
却在经过一处假山时,猛地被斜里伸出的一只脚绊了一下!
“啊!”
她惊呼一声,整个人向前扑倒。
手中捧着的软烟罗瞬间脱手,散落开来,好几匹直接落入了假山旁未干涸的雨后泥泞中!
沈知微摔在地上,手肘磕得生疼,她却顾不得,只惊恐地看着那些沾满污泥的珍贵布料。
“哎呀!
走路不长眼睛吗?”
一个娇俏又带着明显恶意声音响起。
沈知微抬头,看见绊倒她的是个穿着桃红色比甲、容貌娇媚的大丫鬟,她认得,这是书房里伺候笔墨的挽月,颇有些脸面。
挽月身后还跟着两个小丫鬟,正捂着嘴,幸灾乐祸

全家被抄那日,我钻进仇人被窝番外+无删减版
推荐指数:10分
主角是沈知微沈府的精选现代言情《全家被抄那日,我钻进仇人被窝番外+无删减版》,小说作者是“悦柒柒呀”,书中精彩内容是:全家被抄那日,我撕了婚约钻进仇人的被窝。他掐着我脖颈冷笑:「沈小姐以为,本官是那种怜香惜玉的人?」后来「说好要当我正妻的,你骗我...」---1雪粒子砸在窗纸上,簌簌的响,像是无数细密的鬼魂在叩门。沈知微身上最后一件值钱的珠钗也给了押送流放队伍的那个小头目,才换来片刻间隙,藏匿在这座深宅大院后墙的阴......
第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