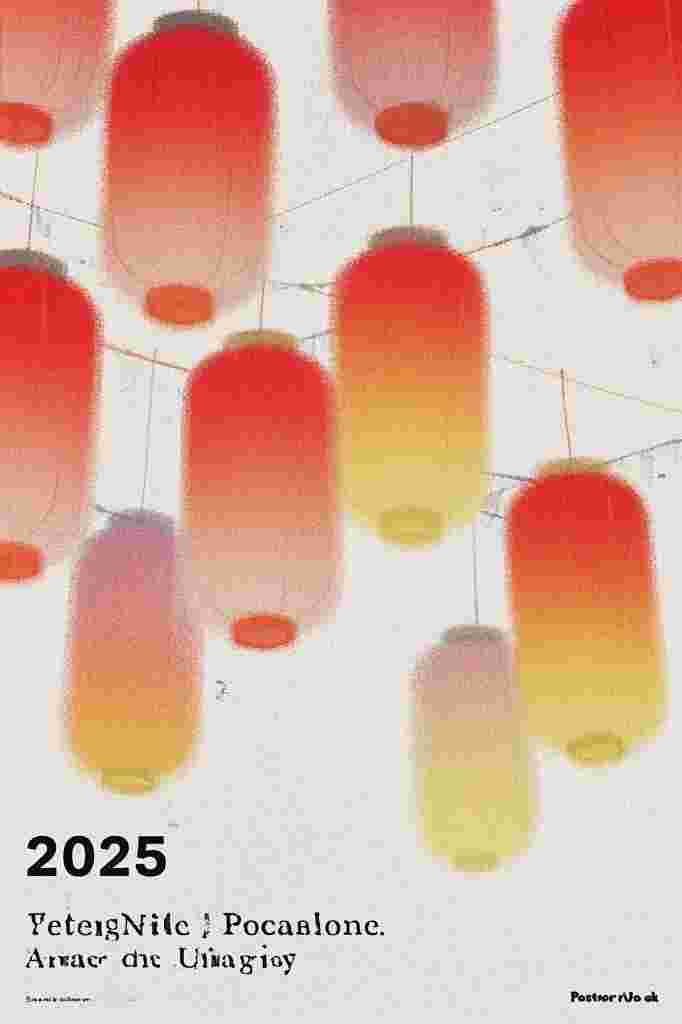海来看过他几次。
第一次来时,他坐在陈星床边的椅子上,手脚似乎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过去的兴奋和大胆从他身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笨拙的沉默。
他没有再提“外星人”、“飞碟”或者任何与之相关的词汇。
“你……好点没?”
小海干巴巴地问,眼睛看着窗外。
“嗯。”
陈星的声音虚弱沙哑。
又是一阵沉默。
“它……后来再没来过。”
小海最终说道,语气里听不出是失望还是庆幸,更像是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与他们两人都已无关的事实。
“哦。”
陈星应了一声。
那次之后,小海来的次数少了,即使来了,话题也变成了即将播出的动画片,或者新学期可能要换的数学老师。
他们之间,多了一层看不见的、薄而坚韧的隔膜。
那个共同的、巨大的秘密没有让他们更亲密,反而像一块过于沉重的巨石,横亘在中间,他们心照不宣地绕开它,因为谁都没有力量再去撬动或谈论它。
一种奇怪的疏远开始弥漫,紧密,因为他们共享着绝无仅有的经历;疏远,因为他们无法就这经历交流任何一个字。
小海的眼神里,多了些陈星看不懂的东西,像是某种过早到来的、对世界复杂性的懵懂认知,以及一丝被超乎想象的事物“击败”后的沉寂。
爷爷在某天傍晚端来一碗冰糖炖梨,放在陈星桌上。
他粗糙的手掌摸了摸孙子的额头,确认热度已经退了。
他浑浊的眼睛看着陈星,似乎想说什么。
陈星抬起头,心里涌起一丝微弱的希望,希望爷爷能再次说出那句谚语,或者任何能解释他梦中混沌的话语。
但爷爷只是咂了咂嘴,最终说道:“病好了,就多出去走走,晒晒太阳。
小子娃,结实得很,别瞎想。”
那扇可能通往古老解释或神秘共鸣的门,也被轻轻关上了。
成人世界用一种温和却坚定的方式,将那个夏夜的异响,重新定义为一场需要被阳光驱散的“瞎想”。
镇上并非完全没有痕迹。
杂货店门口,偶尔还能听到零星的议论。
“听说老张家那晚的狗叫得忒邪乎,结果第二天一看,窝在墙角筛糠呢。”
“是不是后山有什么野物下来了?”
“我看未必,王老五喝醉了那天,非说看见个亮闪闪的东西

掠过麦田的影子:(番外)+(结局)
推荐指数:10分
长篇现代言情《掠过麦田的影子:(番外)+(结局)》,男女主角小海陈星身边发生的故事精彩纷呈,非常值得一读,作者“小名阿疯”所著,主要讲述的是:第一部分:夏日的涟漪记忆里的那个夏天,是被无限拉长的白昼,是被太阳晒得发白的土路,是永无止境的、令人昏昏欲睡的蝉鸣。1998年的清河镇,像一枚被时光遗忘的琥珀,凝固在南方起伏的丘陵与无垠的麦田之间。一切都很慢,慢得仿佛连空气的流动都带着黏稠的阻力。我叫陈星,那一年我十岁。我的整个世界,大抵就是清河镇......
第1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