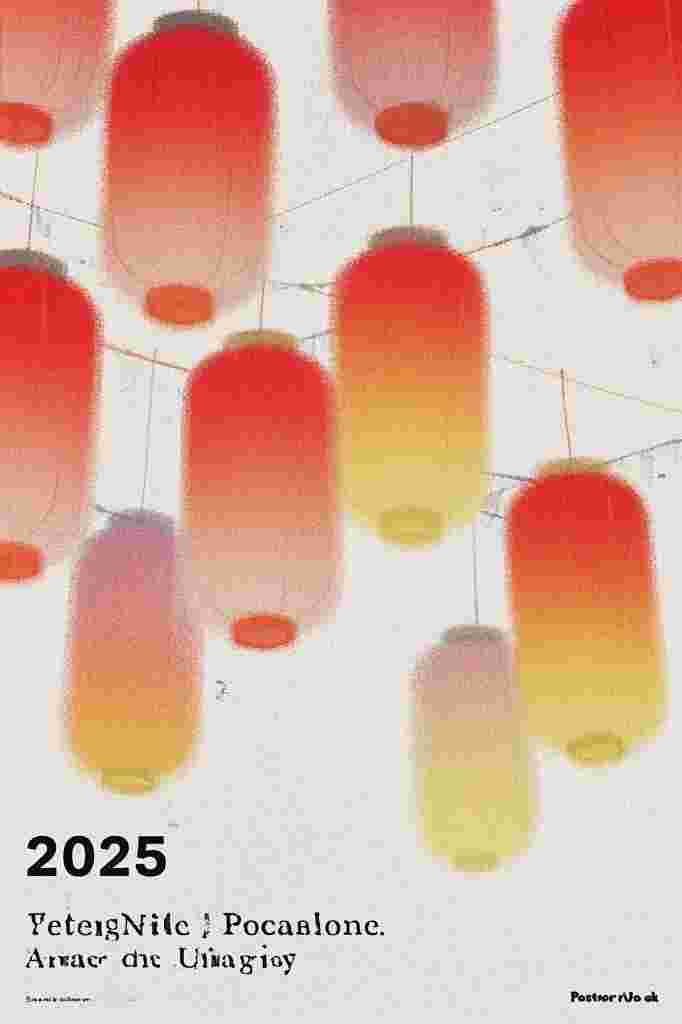薄而均匀,边缘泛着微妙的蓝,在阳光下几乎透明。
我知道这是江花了无数个日夜才磨练出的技艺。
记得他曾告诉我,吹制玻璃最难的在于对温度和时机的把握,太快会破裂,太慢会凝固,就像感情一样需要恰到好处的呵护。
我的目光最终落在那个小小的铃舌上——又来了,他那固执又古怪的仪式感。
我已经熟练到不需要思考。
从工具箱里找出最细的钳子,小心地旋开铃舌底部的微型螺丝。
这个过程我重复了七次,每一次都带着复杂的心情。
有期待,有恐惧,有不解,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感动。
铃舌是空心的,里面照例卷着一小截米白色的纸条。
我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像是要揭开一个重要的秘密,虽然明知那上面只会有一个日期。
“20231027”昨天的日期。
我们第七次分手的日子。
我捏着纸条,靠在墙上,说不清是无奈还是好笑。
这张小小的纸条,这个简单的数字,记录着我们关系中最脆弱的时刻。
每次吵到最凶,我的话像刀子,他的沉默像墙。
我是急脾气,一点就着,而他是慢性格,越是冲突越往心里去。
最后总是以我摔门离开告终。
然后,不超过一天,这只代表“结束”的风铃就会如期而至。
它从不道歉,也不挽留,只是冷静地记录每一次溃败。
甚至有一次和好之后,我窝在他工作室的沙发里,看他给新做的风铃调音。
工作室里弥漫着金属和木材的香气,他专注的侧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柔和。
我忍不住问:“你做这些干嘛?
提醒我们有多能吵?”
他头也没抬,手里的小锤轻轻敲着铜管,发出高低不同的音调:“记录。”
“记录什么?
我的坏脾气和你的闷葫芦?”
我当时语气里带着调侃,但心里确实好奇。
那时他没有回答,只是伸手过来,揉了揉我的头发。
他的手指因为长期工作而略显粗糙,但动作异常轻柔。
后来我也不再问。
每次和好,我都会把这些风铃仔细收起来,放进储藏室的纸箱里。
那是个浅棕色的纸箱,里面铺满了柔软的泡沫粒,现在已经躺着六只不同材质的风铃了——陶瓷的、竹制的、青铜的、贝壳的、不锈钢的,还有上次那只雕花玻璃的。
每一只都代表

风铃全文+后续
推荐指数:10分
现代言情《风铃全文+后续》,主角分别是抖音热门,作者“想染奶奶灰”创作的,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剧情简介如下:1 风铃之谜「这是第七次了,隔壁那个做风铃的男人又送来一只玻璃铃铛。」 每次分手后都会收到他亲手做的风铃,铃舌里藏着我们分手的日期。 我笑他古怪的仪式感,却总在复合后将风铃仔细收进储藏室。 直到某天我提前回家,听见他在工作室对着新做的风铃低语: “这次要做得更结实些,那傻瓜上次摔门时震碎了三只。” ......
第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