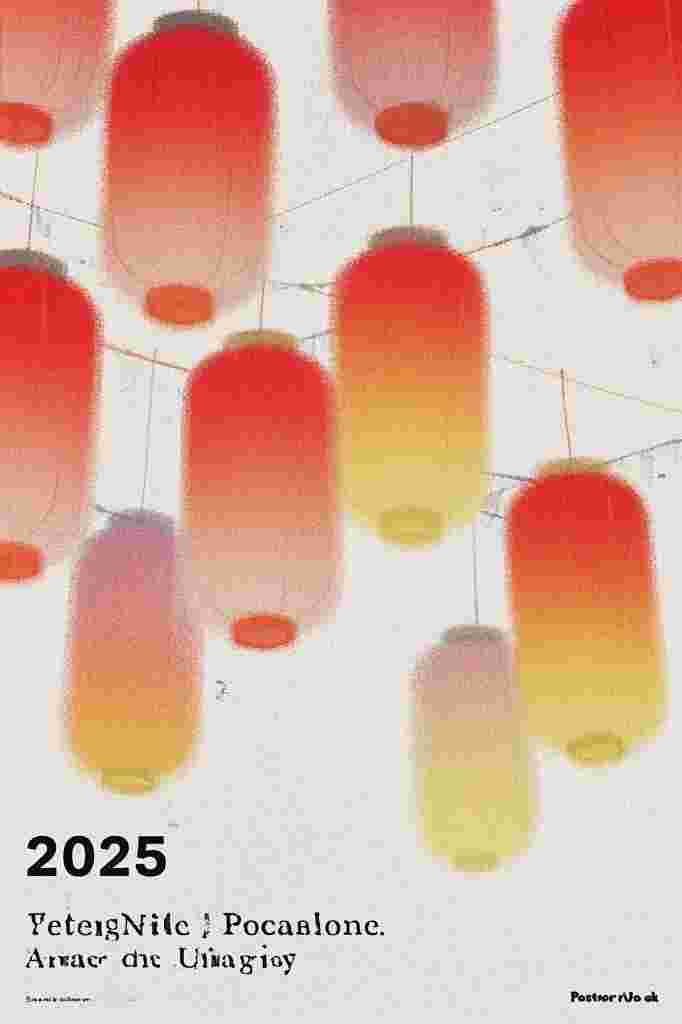,白色的窗帘随着微风轻轻飘动。
我放轻脚步,像个小偷一样靠近。
心里对自己这番行径鄙夷得很,可身体却不听使唤。
我想看看他,哪怕只是远远的一眼,想知道没有我的日子里,他过得好不好。
然后,我听见了。
细微的,几乎被风声掩盖的声响。
是从工作室里传出来的。
叮...叮...咚...是极轻的敲击声,间或夹杂着细微的、类似砂纸打磨的窸窣。
他在家。
在干活。
我心头莫名一松,随即又涌上更深的涩然。
看,没有我,他的一切照旧。
他的风铃照旧。
我凑近那扇半开的窗,借着窗外一丛茂盛的忍冬的遮掩,向内望去。
江背对着窗户,坐在他的工作凳上。
微驼着背,脖颈弯出一个专注的弧度。
他面前的工作架上,悬着一只初具雏形的风铃。
看材质,像是某种深色的金属,也许是铜。
他正用一把极小号的锉刀,极其小心地修整着其中一枚铃铛的边缘。
动作很慢,很轻,充满了某种我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近乎虔诚的谨慎。
然后,我听见了他的低语。
声音太轻了,含混在偶尔响起的金属细微碰撞声里。
但我捕捉到了几个碎片般的词。
“…得更结实些…”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停下手,拿起旁边桌上放着的一件东西,举到眼前细看。
透过忍冬的枝叶缝隙,我看清了——那是一只玻璃风铃,和我门把手上收到的那只一模一样,但铃身布满了清晰的裂纹,像是被什么巨大的力道震裂的。
他凝视着那只破碎的风铃,拇指极轻地抚过裂纹。
接下来那句话,像一枚冰冷的针,猝不及防地刺入我的耳膜。
“那傻瓜上次摔门时…震碎了三只。”
那傻瓜…摔门…震碎了三只…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钝锤,重重砸在我心口。
空气瞬间被抽干,我猛地攥紧了忍冬冰凉的枝叶,枝叶刺痛掌心。
原来他知道。
他知道那只风铃碎了。
他甚至知道是被我摔门震碎的。
他什么都知道。
他不是在记录。
他是在…修补?
还是在为下一次的“震碎”做准备?
做得更结实些?
为了经得起我下一次的摔门离去?
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和冰凉的刺痛瞬间攫住了我。
原来我视若珍宝又厌弃无比的每一次“记录”,在他那里,只是一次

风铃
推荐指数:10分
现代言情《风铃》,男女主角分别是抖音热门,作者“想染奶奶灰”创作的一部优秀男频作品,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剧情简介:1 风铃之谜「这是第七次了,隔壁那个做风铃的男人又送来一只玻璃铃铛。」 每次分手后都会收到他亲手做的风铃,铃舌里藏着我们分手的日期。 我笑他古怪的仪式感,却总在复合后将风铃仔细收进储藏室。 直到某天我提前回家,听见他在工作室对着新做的风铃低语: “这次要做得更结实些,那傻瓜上次摔门时震碎了三只。” ......
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