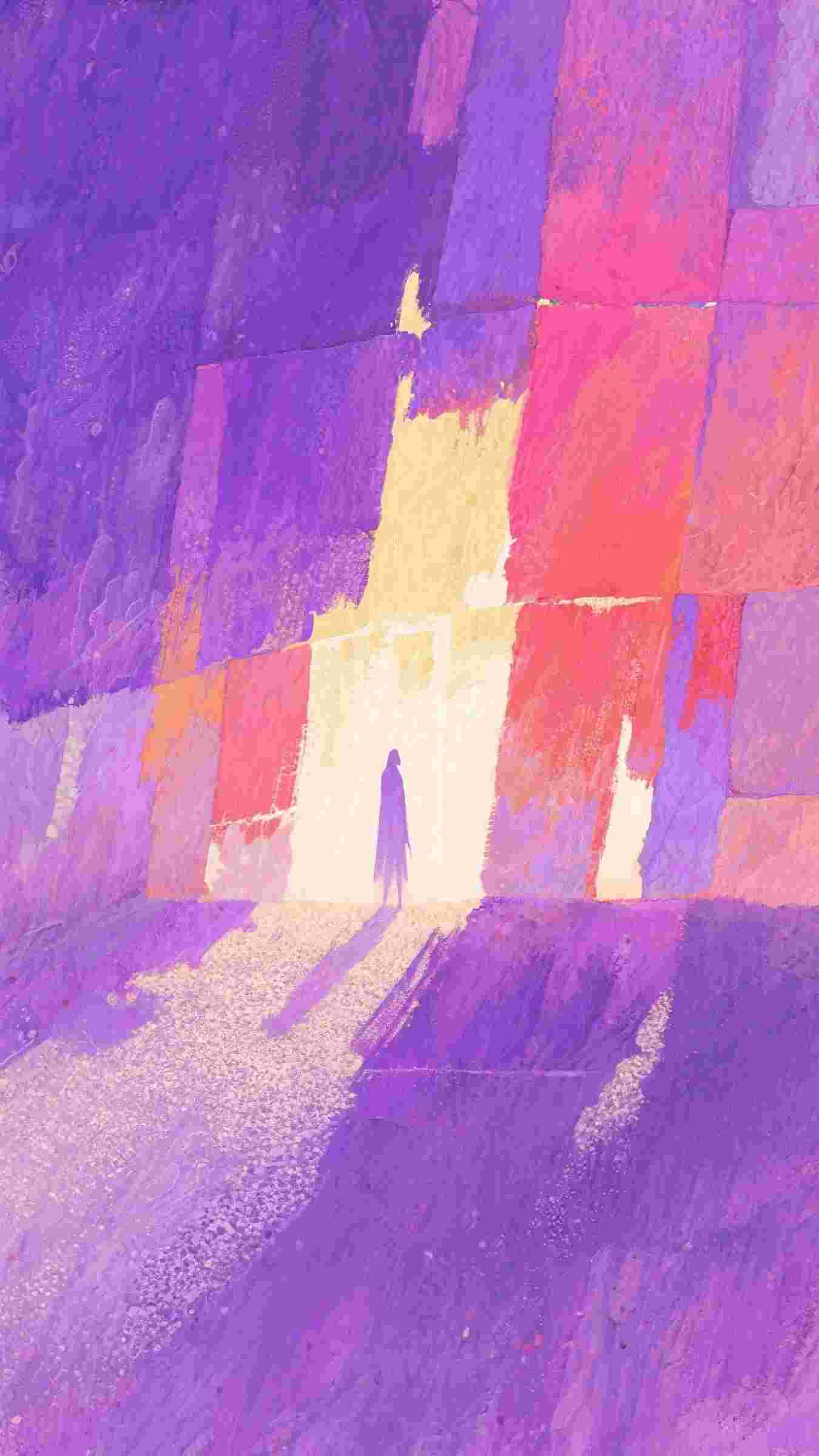板的手臂上,眉头几不可查地蹙了一下。
“能走吗?”
他的声音低沉,听不出什么情绪。
我忍着全身的剧痛,点了点头。
他不再多言,小心地避开的我的伤处,动作轻柔却不容置疑地将我从病床上扶起,用他的风衣裹住我满是血迹和狼狈的病号服。
陈铭这才反应过来,试图上前阻拦:“顾总!
这……这不合适!
温小姐还需要治疗,她的伤很重,而且周总那边……”顾沉舟终于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那眼神如同冰刃,让陈铭瞬间噤声。
“告诉周砚庭,”顾沉舟的声音不高,却带着极强的压迫感,“人,我要了。”
说完,他不再给陈铭任何说话的机会,半扶半抱地带着我,快步离开了病房。
黑色的宾利慕尚平稳地行驶在前往私人机场的路上。
我靠在舒适的后座,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额角和手臂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心里却是一片奇异的平静。
顾沉舟递给我一杯温热的牛奶:“值得吗?”
我接过杯子,指尖感受到恰到好处的温暖。
我笑了笑,嘴角牵扯到额角的伤,有点疼。
“五年青春,换他一场空欢喜,我觉得挺值的。”
他挑眉,侧脸线条冷硬:“计划顺利?”
“嗯,”我轻轻啜饮着牛奶,“他一定会认为我死了,或者至少重伤濒死。
以他的自负和对林薇的沉迷,不会花太多心思深究一个‘替身’的死活。”
“然后呢?”
“然后……”我看着窗外逐渐清晰的机场轮廓,声音轻得像叹息,“看他从他自己堆砌的高处,摔下来。”
……周砚庭发现我不见,是在三天后。
这三天,足够顾沉舟动用私人关系,将我的一切出院、转院记录抹得干干净净,甚至安排了一场疑点重重、最终以“伤者被不明车辆接走”结案的车祸调查。
这三天,也足够周砚庭安抚他受惊的新婚妻子,享受他失而复得的“真爱”。
他打的是我的私人号码,语气是显而易见的不耐烦和惯常的命令式。
“温念,闹脾气也要有个限度。
玩失踪这种把戏,很幼稚。”
我听着电话那头他熟悉的声音,手指轻轻划过平板上关于周氏股票小幅波动的财经新闻,没有出声。
他的耐心显然很快耗尽了,语气变得更差:“薇薇这两天胃口不好,说
金主的白月光给我发了喜帖无删减全文 第7章 试读
爱吃红枣甜酒的上官棠 著 周砚庭林薇现代言情 来源:cddp 时间:2025-08-25 23:37:00

金主的白月光给我发了喜帖无删减全文
推荐指数:10分
现代言情《金主的白月光给我发了喜帖无删减全文》,现已完结,主要人物是周砚庭林薇,文章的原创作者叫做“爱吃红枣甜酒的上官棠”,非常的有看点,小说精彩剧情讲述的是:周砚庭结婚那天,我亲手给他做了蛋糕。窗外,北城的盛夏骄阳似火,蝉鸣声嘶力竭,仿佛也要为这场举世瞩目的婚礼燃尽最后一丝生命。室内,冷气开得很足,甚至让我裸露的胳膊起了一层细密的疙瘩。我系着那条他曾经说像“家里小保姆”的碎花围裙,站在料理台前,小心地用抹刀将最后一点淡奶油抹平。空气里弥漫着甜腻的奶香和新......
第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