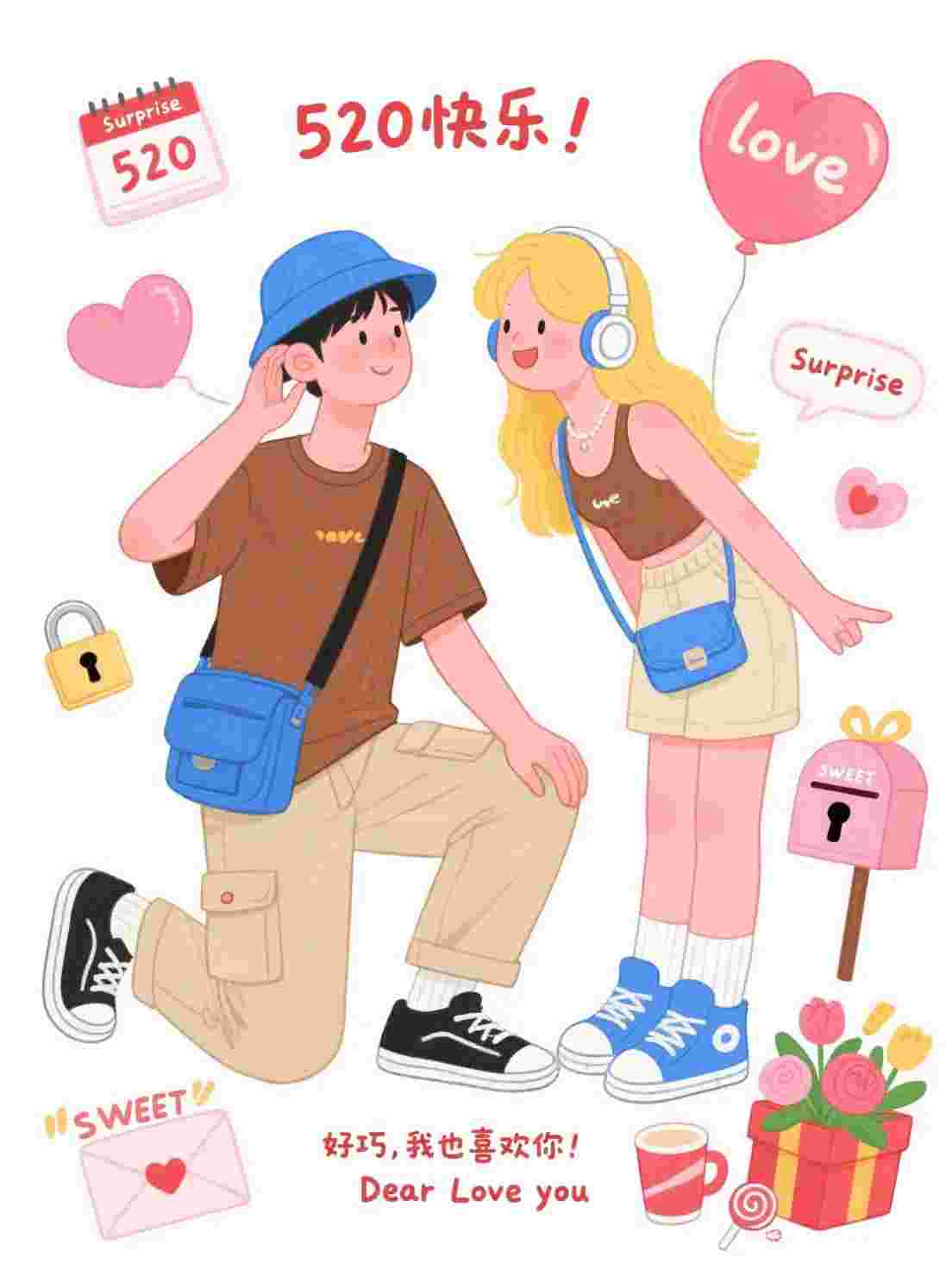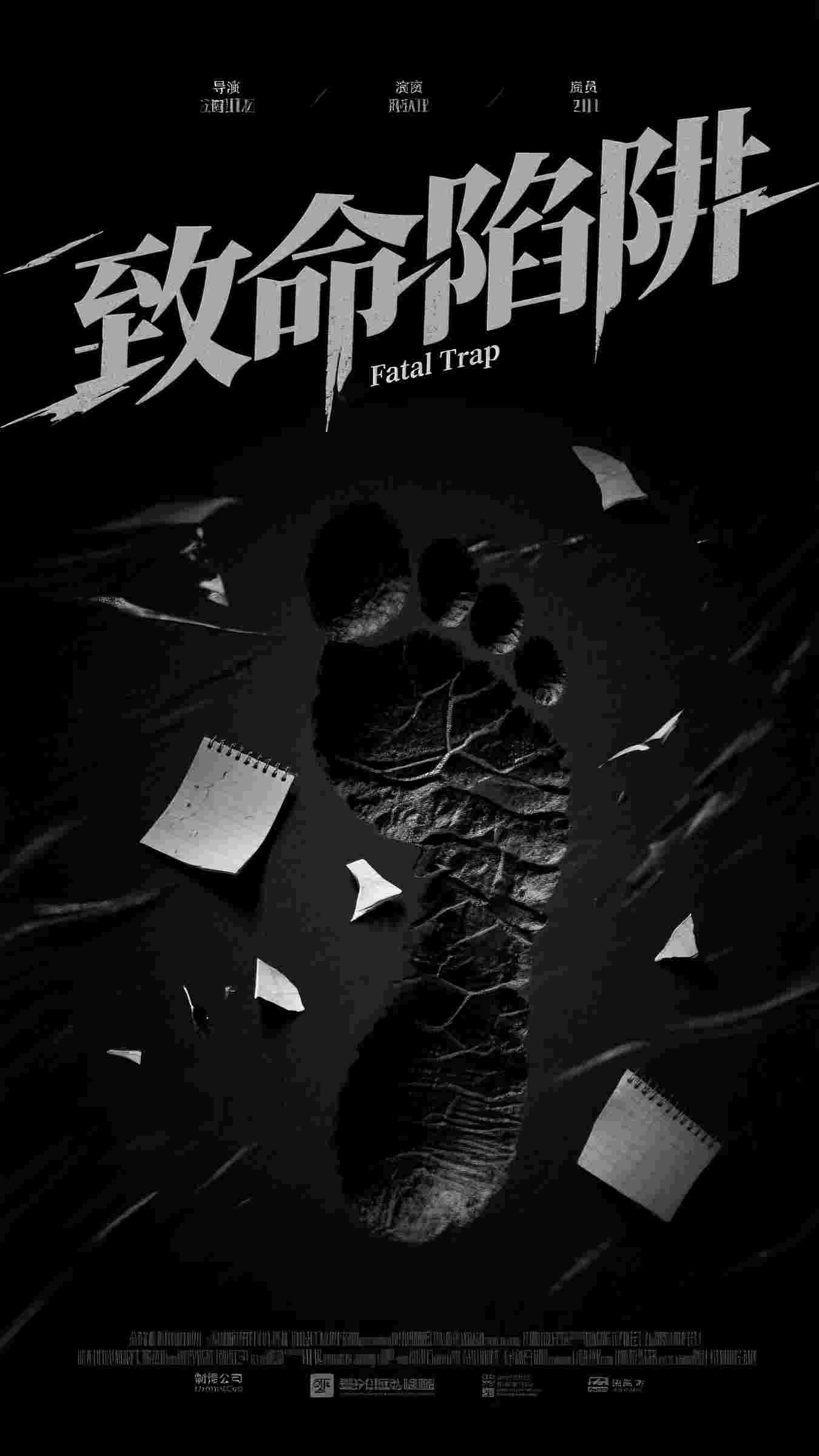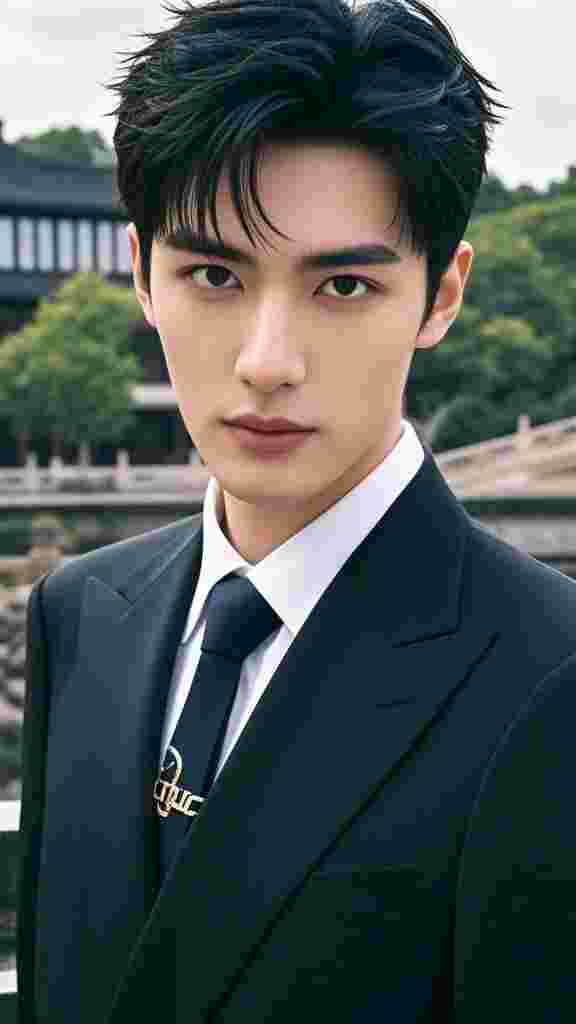边是矿车轰隆、汽笛嘶鸣的交响曲。
他的行囊简单,一卷铺盖,几件旧衣,还有一颗被父亲那句“下井的,都是真汉子”鼓动得砰砰直跳的心。
报到,领装备——一盏沉重的矿灯,一身粗布工作服,一双高帮胶鞋。
老工长眯着眼打量这个结实得像小牛犊的后生,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煤衬得雪白的牙:“娃,有力气就行!
跟着我,炮工班正缺人!”
井下是另一个世界。
罐笼轰隆隆地沉入地心,黑暗如同实质般挤压过来,只有头顶矿灯那一点微弱的光晕,是唯一的安全区。
打眼、装药、放炮——这是他的日常工作。
风钻在岩壁上嘶吼,震得虎口崩裂;放炮后煤尘弥漫,几步之外不见人影,呼吸一口,肺里就像塞进了一把沙砾。
一个班下来,除了眼白和牙齿,全身都是墨黑。
升井后,没有澡堂,锅炉房打点热水,端个脸盆在工棚外擦洗,一盆水立刻变得像墨汁一样。
最难受的是渴。
井下高温,汗水能把衣服浸透好几回。
带下去的水壶早就见了底。
“渴急了,就瞅着煤壁上渗出的水珠,凑上去接两滴,或者干脆舔一舔那湿漉漉的煤壁。”
多年后,张永平对记者说起这段,对方脸上难以置信的表情让他有些“傲娇”地笑了:“那算什么?
我们煤矿工人最不怕的就是吃苦!”
苦,是真苦。
但年轻的身体里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看着一车车乌金被运出地面,他心里萌生出一股原始的骄傲。
1992年的一天,队里宣传干事下井,抓拍了一张照片:前景是张永平,戴着磕瘪了的安全帽,满脸乌黑,正抡着大锤敲打一根支柱,汗水和煤泥在他年轻的脸上冲出道道沟壑,眼神却专注而锐利,仿佛在跟眼前的钢铁和煤炭较劲,也像是在跟这个世界宣告他的存在。
那张照片,后来被他珍藏了起来。
那是他青春的印记,是闯入这个黑白世界的通行证。
二、硬骨头与亮眼光(1993-2009)踏实、肯干、还有股遇到难题就非要钻透的拧劲儿,张永平很快从一群青工里冒了头。
他不再满足于只是出力气打眼放炮,休息时总围着老师傅转,问这问那:为什么炮眼要打这个角度?
怎么从岩层的声响判断是不是结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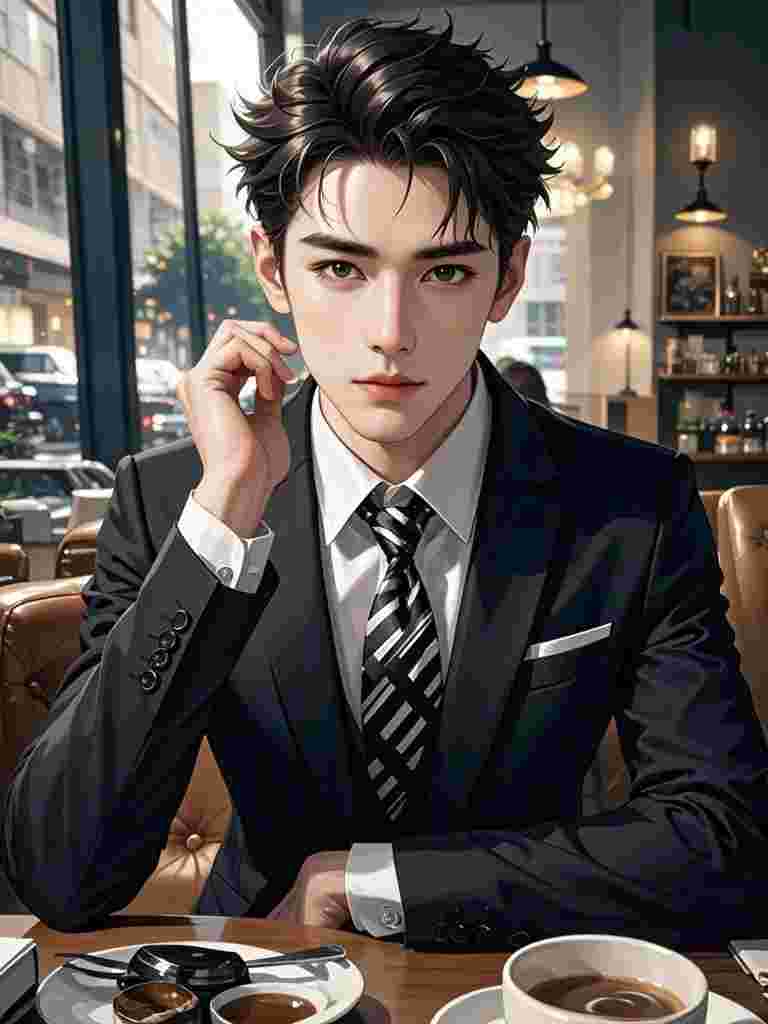
90年代,我在山西当煤炭工人王保田热门全集
推荐指数:10分
正在连载中的现代言情《90年代,我在山西当煤炭工人王保田热门全集》,热血十足!主人公分别是王保田热门,由大神作者“小雅看风景”精心所写,故事精彩内容讲述的是:深井之下,父辈的煤九十年代的山西煤矿深处,我以为挖煤只是枯燥的苦力,直到目睹老矿工在坍塌事故中为救新手而牺牲,才惊觉黑暗的井下燃烧着最耀眼的人性光辉;而我最终接过他的遗志,在每一次巷道穿行中,学会了如何在地下黑暗中寻找光明。(一)一九九0年的春天,风里还裹着冬末的渣子,刮过吕梁山麓,吹得矿区的彩旗裤......
第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