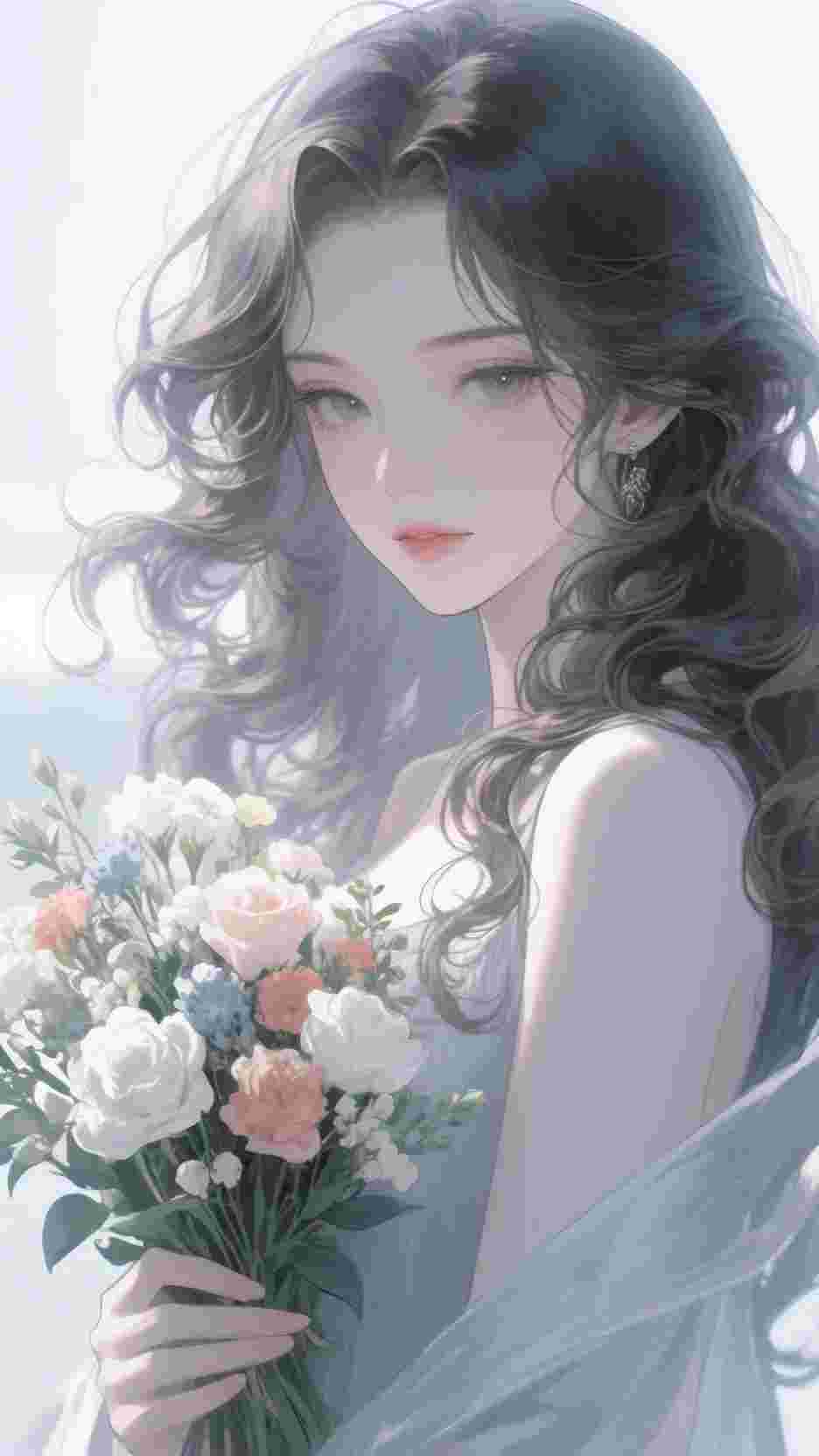有下雪,但风很大,吹得松涛阵阵,像是有人在哭。
墓前只站着几个人。
我,陈宿,还有苏锦白。
卫家班的人一个没来。
他们大概还在为争夺班主的位置,斗得头破血流。
陈宿盘腿坐在墓前,将胡琴放在腿上。
他试了试音,然后对我点了点头。
我整理了一下衣袍,走到墓碑前。
没有锣鼓,没有配乐,只有一人的清唱,和一人的胡琴。
我闭上眼,再睁开时,我不再是裴安。
我是白素贞。
“西湖山水还依旧……”我一开口,苏锦白就愣住了。
我的声音,清亮,婉转,却又带着一种穿透骨髓的悲凉。
陈宿的胡琴声适时地响起,如泣如诉,像是缠绕在白素贞身上的千年孤寂。
我唱的,是陈宿和林霜月写的那个版本。
词句更加凄美,情感更加浓烈。
从“断桥相会”的缱绻,到“盗取仙草”的决绝,再到“水漫金山”的癫狂。
最后,我唱到了那句关键的唱词。
“……恨只恨,恩情一朝改,旧盟非昨。”
唱出这一句时,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女子,站在断桥上,望着远去的孤帆,泪流满面。
她恨的不是许仙薄情,而是命运弄人,恩情更改,昨日的盟誓,都成了泡影。
这才是这出戏的魂。
一曲唱罢,天地无声。
只有风,吹过我的衣角。
陈宿收起胡琴,站了起来。
他走到墓碑前,伸手,轻轻拂去碑上的尘土。
碑上刻着“爱妻林霜月之墓,夫卫宏正立”。
陈宿看着那个“夫”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酒瓶,将里面的酒,缓缓地洒在墓碑前。
“霜月,我来看你了。”
“我把儿子养大了,他比我唱得好。”
“你在那边,安息吧。”
说完,他转过身,对我和苏锦白说:“走吧。”
我们没有再回头。
下山的路上,苏锦白问我:“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接手卫家班。”
我说。
苏锦白有些惊讶。
“但它不再叫卫家班。”
我看着远处夕阳下的京城,一字一顿地说,“它要改名叫南华班。”
我要让南华戏楼,重新响遍京城。
我要让陈宿和林霜月的戏,被世人听见。
这,才是我对他,最好的报答。
12.接手卫家班的过程,比我想象中要艰难。
卫宏正一死,人心散了。
几个台柱子各自拉拢了一批人,另

被逐出师门后,师傅求我唱完残曲卫宏正裴安(番外)+(结局)
推荐指数:10分
“汉堡汉堡憨包”的《被逐出师门后,师傅求我唱完残曲卫宏正裴安(番外)+(结局)》小说内容丰富。精彩章节节选:我是师父卫宏正最得意的弟子,梨园行公认的下一代翘楚。他逢人便夸我,说我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可就在那年冬天,汇报演出,一折《断桥》,我唱错半句戏词。师父当着满后台人的面,将我逐出梨园。大雪封城,我无处可去,最终走进城南那座废弃的戏楼。看守戏楼的陈老板是个酒鬼,脾气古怪,据说年轻时唱坏了嗓子,最恨唱戏......
第10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