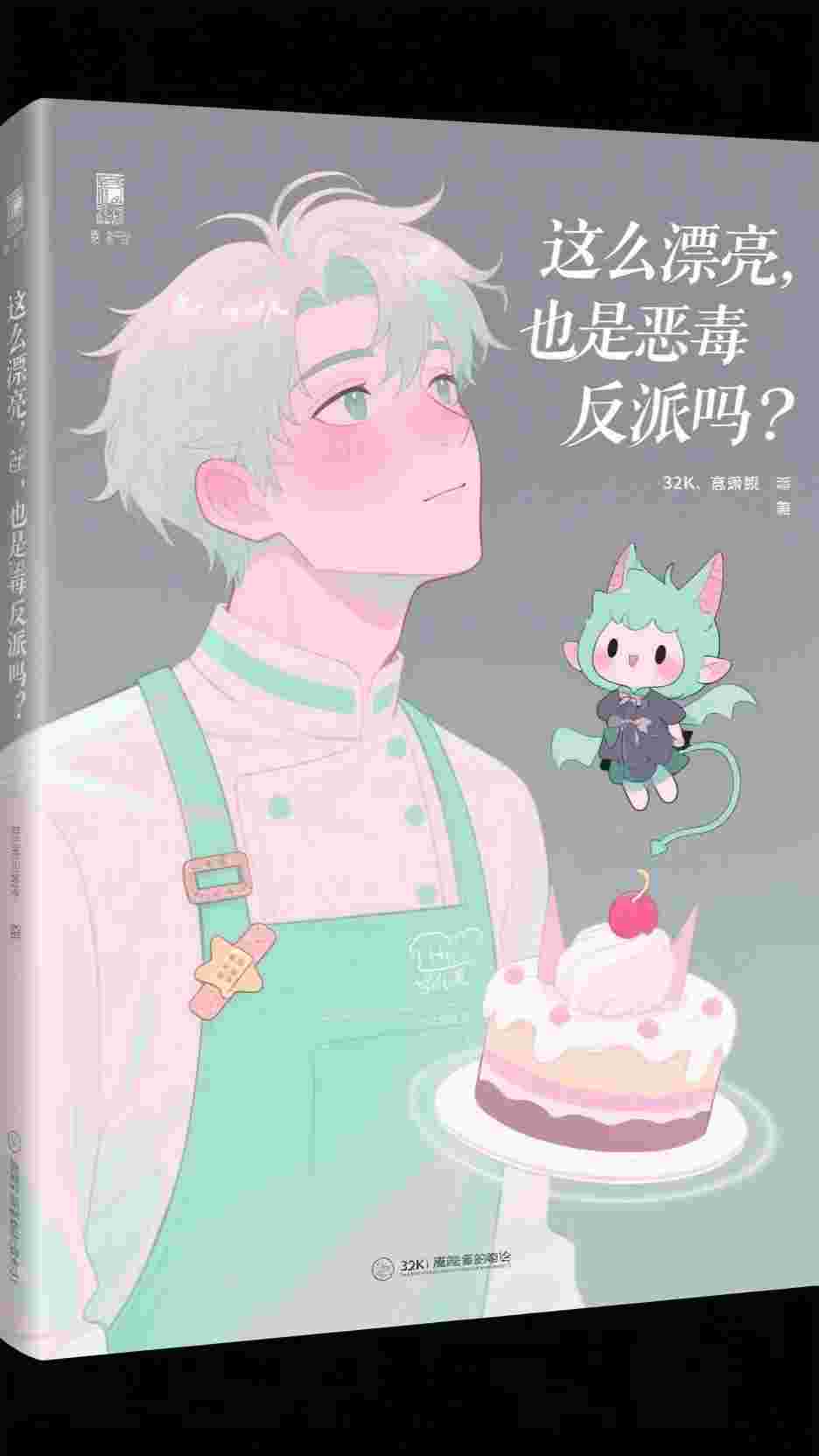,提前病退了。
那栋他们住了十几年的三层小楼,也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到了我的名下。
陈卫东来找过我一次。
那天我正在收拾新家,他站在门口,胡子拉碴,整个人憔悴了一大圈。
“禾禾,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
他声音沙哑地问。
我连头都懒得抬,“你说呢?”
“巧巧她……她只是一时糊涂。”
他还在为周巧巧辩解,“她从小在乡下吃苦,没过过好日子,所以才……所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我当猴耍?”
我停下手里的活,冷冷地看着他,“陈卫东,你不是蠢,你就是坏。
你早就知道她在装病,你只是在配合她,享受着掌控我的快感。”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我没有!”
他急切地否认。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想再跟他废话,“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院子的大门。
我以为他会纠缠,但他没有。
后来我听王姨说,陈卫东被调走了,去了西北最偏远的一个哨所。
听说,是他自己申请的。
而周巧巧,也被她父母送回了乡下老家。
曾经风光无限的陈家,就这么散了。
我搬进新家的那天,陆骁来了。
他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了一件白衬衫和一条军绿色的裤子,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温和。
他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是两瓶茅台。
“恭喜乔迁。”
他说。
“谢谢。”
我接过酒,给他倒了杯水,“快请坐。”
他打量着被我收拾得焕然一新的屋子,点了点头:“很干净。”
“你今天不忙吗?”
我问。
“今天休息。”
他喝了口水,看着我,眼神认真,“姜禾,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的心,没来由地漏跳了一拍。
“你说。”
他沉默了片刻,似乎在组织语言。
“我母亲,很喜欢你。”
“嗯,我也很喜欢周奶奶。”
“她希望,你能成为她的儿媳妇。”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他……这是在替他母亲传话,还是……“当然,”他看着我,黑曜石般的眸子里,映着我惊慌失措的脸,“这也是我的意思。”
“姜禾同志,我,陆骁,三十岁,团级干部,无不良嗜好,会把工资和津贴全部上交。
我希望,你能以结婚为前提,和我

不做恋爱脑,军区首长的掌中宝陈卫东姜禾:前文+后续
推荐指数:10分
热门小说《不做恋爱脑,军区首长的掌中宝陈卫东姜禾:前文+后续》是作者“嘉喜WEY”倾心创作,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这本小说的主角是陈卫东姜禾,情节引人入胜,非常推荐。主要讲的是:订婚宴上,那个刚被认回来的真千金周巧巧又晕了。我那二十四孝好未婚夫陈卫东,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掐着我的腰,红着眼低吼:“姜禾,巧巧快不行了,你现在、立刻、马上去给她做饭!”他滚烫的呼吸喷在我耳廓,话语里却满是威胁,“不然今晚的洞房,我让你下不了床!”我笑了,当着他和他全家的面,把他送我的金戒指褪下来,......
第1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