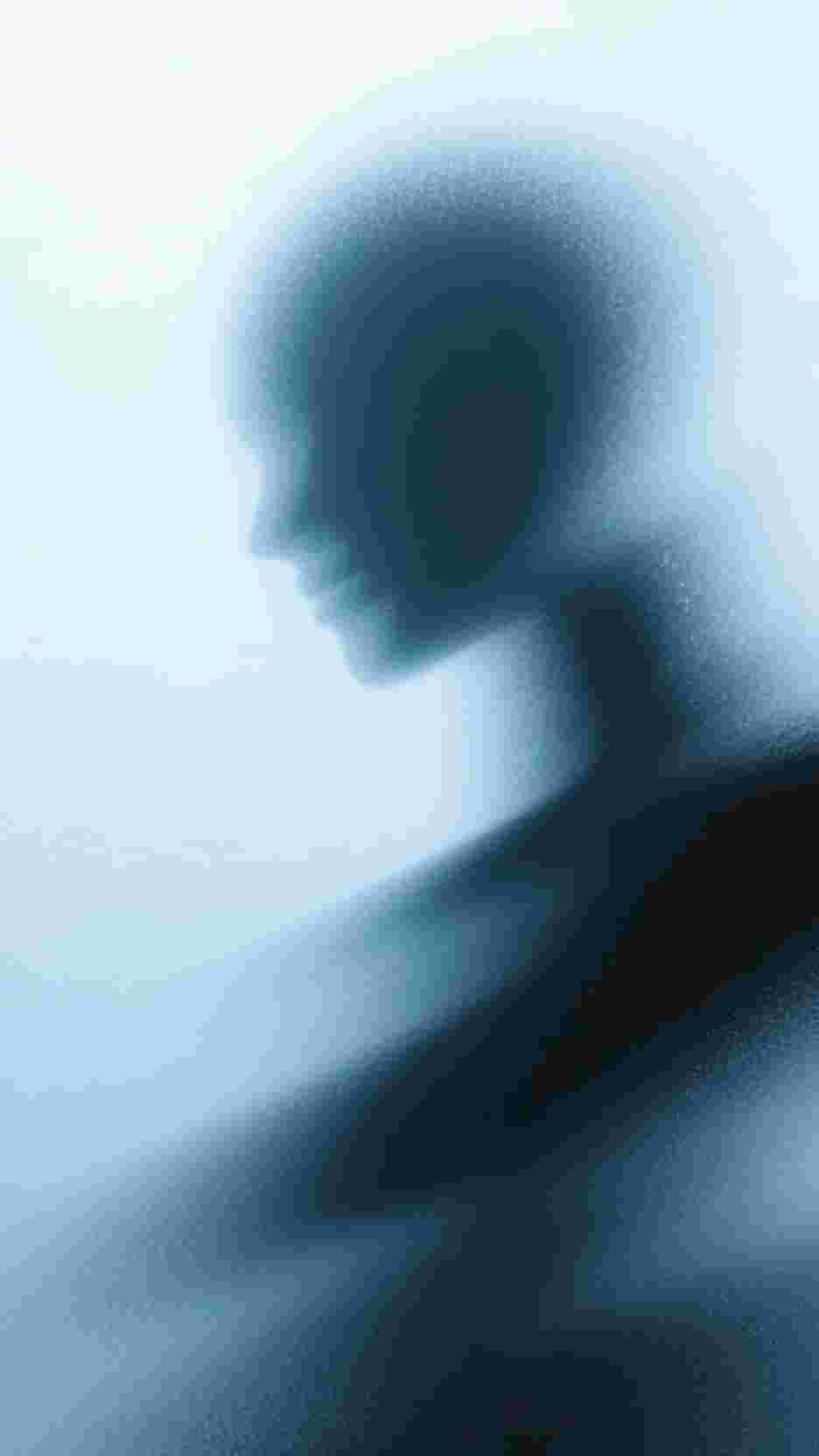黑暗逐渐吞噬了房间。
我坐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像一个迷失在巨大迷宫入口的人,眼前的道路非但没有清晰,反而涌出了更多扑朔迷离的岔路。
顾屿的失控,顾母的回避,那个压在所有人身上、似乎一旦曝露就会天崩地裂的“秘密”……它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我们所有人牢牢困在其中,十年不得解脱。
而我这只废掉的手,阴差阳错地,成了撕开这张网的第一道裂口。
我抬起左手,轻轻放在冰冷的石膏上。
必须好起来。
我必须,亲自找出答案。
电话里的忙音像最后一丝天光被掐灭,病房彻底沉入昏暗。
顾阿姨那疲惫、回避,甚至带着一丝古怪劝诫的声音,还在耳边嗡嗡作响。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小屿他……也不容易。”
“放下了,对大家都好。”
每一个字都像一块沉重的、形状诡异的积木,胡乱堆叠在我原本以为清晰的认知高塔上,摇摇欲坠。
恨是简单的,愧疚也是简单的。
可这不是恨,也不是单纯的宽恕。
这是一种更深沉、更粘稠、缠绕所有人十年的东西。
它叫秘密。
右手石膏的冰冷透过薄薄的病号服,渗进皮肤,冻得我轻轻一颤。
我必须知道。
不仅仅是为了这只手,更是为了从这巨大的、令人窒息的谜团里挣脱出去。
复健变得近乎自虐。
每天最早到,最晚走。
复健师设计的温和课程被我私自加码到极限。
咬着牙,额头颈间青筋暴起,汗珠大颗滚落,砸在训练器械冰冷的金属杆上。
每一次微小的移动,都像有无数细小的钢针在筋肉神经里搅动,痛得眼前发黑,几欲呕吐。
“安小姐,慢一点,真的不能急!”
复健师第三次按住我颤抖不已的手臂,眼里是真切的担忧和不解,“神经恢复有自己的节奏,过度训练反而会造成二次损伤!”
我喘着粗气,眼前一片模糊的水光,说不出话,只是固执地摇头。
慢不了。
顾屿门外那句嘶吼是倒计时。
顾阿姨语焉不详的回避是催化剂。
我没有时间。
偶尔,在痛到极致、意识涣散的边缘,我会猛地抬起头,视线扫向复健室外那扇长方形的玻璃窗。
空的时候多。
但有过那么一两次,窗边有人影倏地闪过,快得几乎以为是错觉。
只有一

谎奏终章番外+无删减版
推荐指数:10分
看过很多现代言情,但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谎奏终章番外+无删减版》,这是“嬴十六”写的,人物林姐肖邦身上充满魅力,叫人喜欢,小说精彩内容概括:我以为他是恨我的,毕竟十年前是我父亲害死了他姐姐。 十年间他总在我登台演奏钢琴时坐在角落,目光淬毒般刺向我。 直到我为救他右手重伤,再也无法弹琴。 病房外,我听见他疯狂哀求医生:“必须治好她!” “她若不能弹琴……我隐瞒十年的秘密……就再也藏不住了……”---剧院里的空气是冷的,凝着一种近乎神圣的肃......
第10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