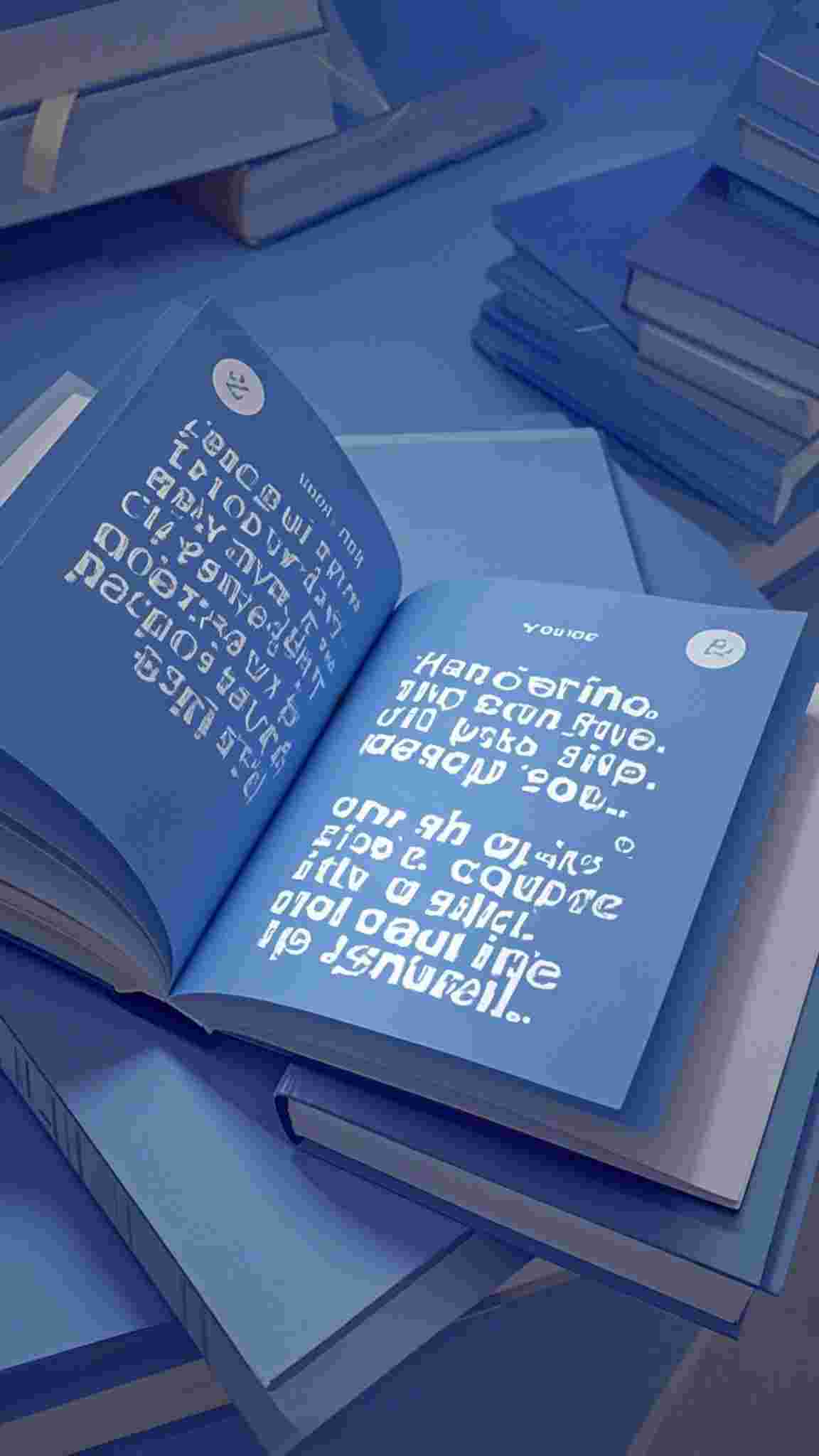小子硬闯高级场所被扔出门”的社死画面。
幸好,机器最后还是绿了,他挥挥手放行,眼神里带着点“这年头什么人都能当评论家”的意味。
我松了半口气,另半口还吊在嗓子眼。
进去之后周围全是所谓的“成功人士”,谈笑风生,动不动就“后现代解构”和“流动性叙事”。
我就像个误入天鹅湖的丑小鸭,只能努力回忆画家那种目空一切的德行,挺直腰板,眼神放空,从侍者盘子里拿了杯香槟,这纯道具,一口没敢喝,怕露怯。
转悠了一会,就看到一堆人围着一个粉色丝绒西装的男子,定睛一看那个人就是李铭,高一堆文围着他谈阔论,但他眉宇间透着股不耐烦,应该是时间过长显得有点疲惫。
我假装欣赏旁边一幅用了大量蓝色的画作,不得不说,画家记忆让我一眼就看出这蓝色用得俗不可耐。
我调整角度,确保李铭能听到,然后用一种不高不低、刚好能透出鄙夷的语调自言自语:“试图用克莱因蓝表达深邃?
可惜纯度不够,层次单一,徒有其表,流于肤浅。”
李铭果然被吸引了,或者说,被这种直白的冒犯勾起了兴趣。
他挑眉看过来:“哦?
你觉得这幅《忧郁的河》用的蓝不对?”
我压下心跳,刻意模仿着画家那种刻薄的调调,甚至带上了他对于“昂贵材料”的执念:“钴蓝?
不,这是廉价的群青滥竽充数。
真正的忧郁,需要更纯粹、更昂贵的蓝色来献祭。”
李铭果然觉得我这“毒舌”人设有点意思,挥退了身边奉承的人,凑近了些。
谈话间,我故意把话题往神秘学、稀有体验、超越常规的刺激上引,老周分析过,这种被宠坏的富二代就好这口。
他果然上道,压低声音,带着一种炫耀式的神秘感:“真正的艺术和极致体验,都在寻常人看不到的地方。
比如某些…‘沙龙’。”
我心里慌得不行,但面上却风轻云淡,甚至恰到好处地露出一丝轻蔑:“哦?
我以为那种地方只存在于三流小说里。”
他被我这态度激怒了,但很快又意道:“下周三,我带你去开开眼。
不过,需要一点‘小小的装扮’。”
他暗示了下面具。
就在我以为快要得手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
邵先生的另一

开局卖身,客户竟是已故好友:全章+后续
推荐指数:10分
《开局卖身,客户竟是已故好友:全章+后续》中的人物抖音热门拥有超高的人气,收获不少粉丝。作为一部现代言情,“三圆一方”创作的内容还是有趣的,不做作,以下是《开局卖身,客户竟是已故好友:全章+后续》内容概括:我穷得只剩下一具健康的身体了。于是我在暗网挂了广告:“身体出租,按小时计费,用途不限。”第一个订单来了:“租用你的手,帮我杀个人。”而客户的名字,是三天前车祸身亡的我发小。01我叫林黯,男,今年22岁,一年前我母亲得了重病,因为家里没钱,期间一直在家里养着,慢慢地母亲地病情越来越严重,去了趟医院,一......
第1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