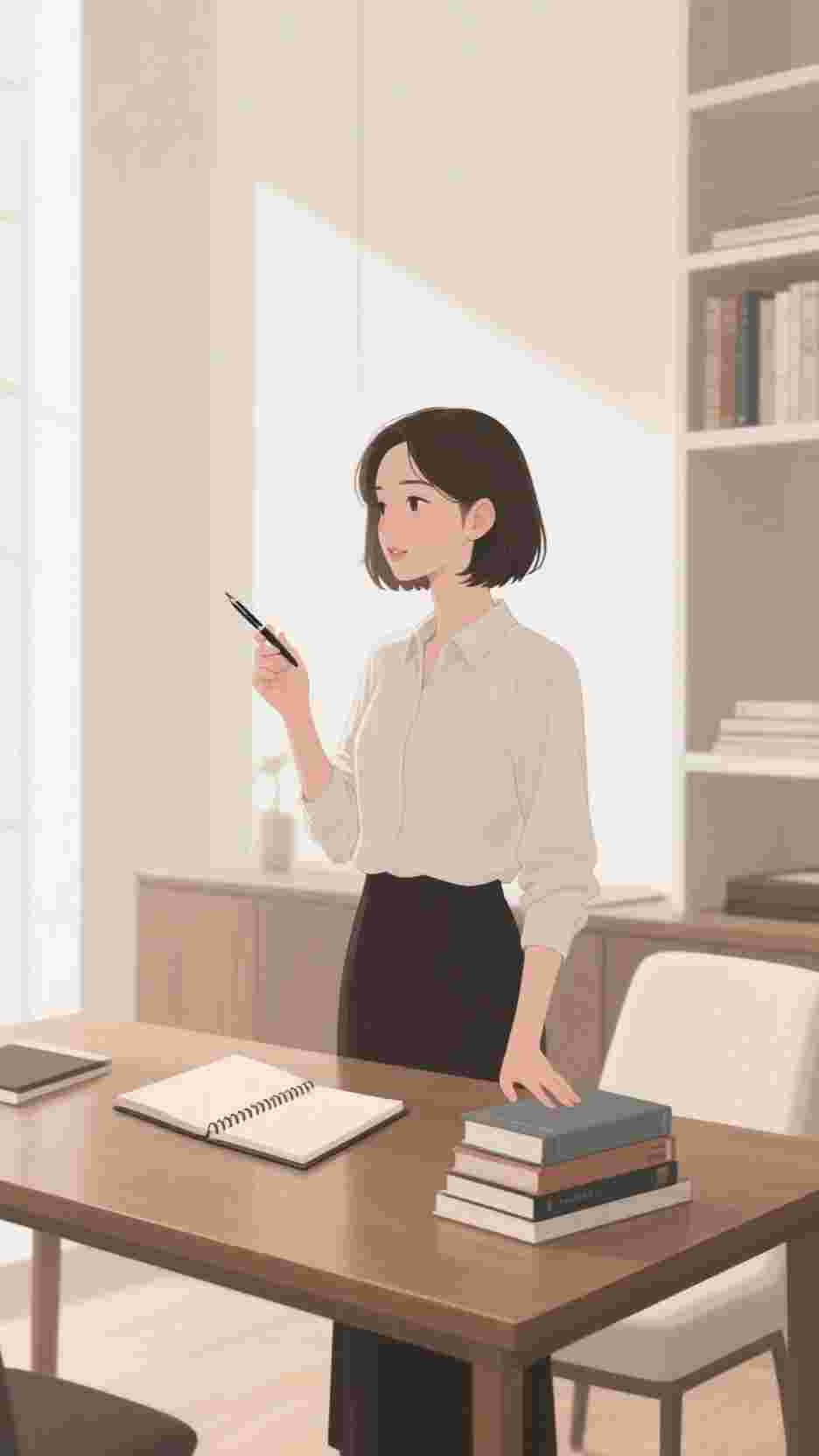她抬起头,想笑一笑,嘴角却怎么也扬不起来,只能低低地说:“是吗?那下次我少放点盐。”
厉修庭没接话,拿起椅背上的外套搭在胳膊上,往门口走:“我出去一趟。”
“欸,你饭还没吃完呢……”刘佩芳的话追着他的背影,却被“砰”的关门声打断了。
可可看着门口,小声说:“爸爸又去找战友喝酒了?”
乐乐舔了舔嘴角的油渍:“可能吧。”
刘佩芳看着桌上几乎没动的带鱼,又看了看自己身上这条浅黄色的裙子,突然觉得有点冷。
她站起身,拿起围裙重新系上,把剩下的菜倒进盘子里,端起来往厨房走。
“我去把菜收起来,你们吃完了把碗筷收拾一下。”她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只是走到厨房门口时,脚步顿了顿,抬手按了按眼角。
厨房里的水龙头开着,哗哗的水流声里,好像能听见自己心里那点刚冒头就被掐灭的欢喜,正一点点沉下去,沉到冰凉的水底。
周末的午后,日头正烈,海风卷着咸腥气扑在饭馆的玻璃窗上。
桑萤系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额角沁着细汗,手里的托盘差点没端稳。
“桑老板,再来盘辣炒蛤蜊!”
靠窗的男人嗓门洪亮,桑萤应了声好,转身时腰撞在门框上,疼得她龇牙咧嘴。
隔壁小酒馆的声音像长了腿,顺着半开的后窗钻进来,一下下敲在她心上。
“厉队,你这脸拉得能挂油瓶了,”是陆延的声音,带着点戏谑,“好不容易休个周末,不琢磨着带可可乐乐去海边玩,非拉着我们喝这苦酒?”
桑萤记得陆延正是本书男主,叶莉莉的丈夫。
崔浩然跟着笑:“可不是嘛,每次休息都这样,酒杯一拿就不撒手。老厉,你这是跟谁置气呢?”
桑萤正往盘子里盛海菜凉粉,手一抖,半勺醋倒多了。
她听见陆延压低声音,却故意让桌边人都听见:“还能有谁?不就是隔壁那位呗。我说厉队,你也是心太软,那种女人……”
“啧,”
有人打断他,“过去五年多疯啊,穿着红裙子跟洋人跳舞,半夜还往招待所跑,全岛谁不知道?现在倒好,开起饭馆来了,装得跟个贤妻良母似的。”
桑萤的脸烧得厉害,指尖捏着盘子边缘发白。
那五年不是她,是另一个魂魄借着她的身子作妖。
可谁信呢?
连她自己都觉得那些荒唐事像场醒不来的噩梦。
“我打赌她改不了,”有人拍着桌子,“玩野了的心,哪能说收就收?听说前阵子还有个金发洋人找她,骑着个大摩托,在饭馆门口转了好几圈呢。”
“这也太猖狂了!”崔浩然的声音陡然拔高,“破坏军婚可是重罪,真要查实了,抓起来都不为过!”
“那洋人不好办吧?”
“有啥不好办的?”陆延哼了声,“厉队可是守岛部队的尖刀,真要动真格的,一个洋人算什么?我看啊,厉队就是太念旧,舍不得那点情分。”
“对待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要么打一顿要么扫地出门!”
“就是,以厉队的条件,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文工团的姑娘们一个个翘首以盼呢!”
桑萤端着盘子往大堂走,脚下像踩着棉花。
她知道厉修庭就在隔壁,隔着一堵墙。
他肯定也听到这些话了。
“说起来,佩芳姐多好,”有人换了个话题,语气缓和下来,“上周我看见她给乐乐送虎头鞋,针脚绣得那叫一个细。人老实本分,又会疼人,比某些整天招摇的强多了。”

军婚冷战五年,扯证离婚他悔红眼后续+完结
推荐指数:10分
现代言情《军婚冷战五年,扯证离婚他悔红眼后续+完结》,由网络作家“苍山行”近期更新完结,主角桑萤厉修庭,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军婚双洁】【破镜重圆】【父子火葬场】桑萤的身体被穿越女占领五年,穿越女用她的身体吃喝玩乐不管孩子,甚至在外面养情夫!桑萤把自己身体抢回来的时候,正好被首长老公捉奸在床。厉修庭双眼猩红:“你如果想离婚,现在就可以离!”桑萤:“我不离了!”这时她才知道,自己是一本年代文里的大反派的早死发妻。在她死后,厉修庭性情大变,成了那令人恐惧的阴鸷大反派。两个孩子也因为无人管教,受人欺凌,下场凄惨。都是因为系统故障,穿越女穿到了她身上。抢回身体后,桑萤打算好好跟首长老公过日子,弥补那缺失的五年。厉修庭却不相信她能悔过,毕竟她闹离婚闹了五年,始终对她冷眼相待。孩子也由他的小青梅抚养长大,巴不得认青梅做亲妈,对桑萤这个亲妈很疏远。桑萤忍无可忍,终于再次提出离婚。但这次,厉修庭却把她堵在身下,发狂的,粗暴的吻遍她全身:“离婚?想都别想!”...
第46章